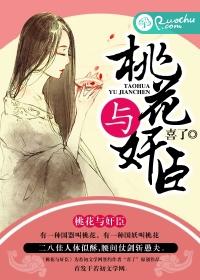BL小说>草芥称王 > 第107章 捕青梅(第1页)
第107章 捕青梅(第1页)
李有才歪在铺着墨色绒毯的楠木榻上,薄衾下隐约露出一角月白的里衣。
他双眼微闭,连呼吸都透着几分无力,活脱脱一副被病魔抽干了精气神的模样。
杨灿陪着何有真去了苍狼峡,青梅身为内管家,自然承担。。。
夜色如墨,终南山巅的无纹钟静静悬于风中,未响。于睿站在钟下,左手紧攥衣袖,遮掩那道已爬至肘弯的黑线。它不再缓慢游移,而是像有生命般搏动,仿佛皮肉之下藏着一条蛰伏的蛇,正一点点苏醒。
他闭眼,深吸一口山间清寒之气。三年来,他每夜饮醒神露压制莲种反噬,加灵鼠之血后虽延缓其觉醒,却也引出了更多不属于他的记忆碎片??那些哀嚎、铁笼、注射针管的画面,如同毒藤缠绕心神,越挣越紧。
“你听见了吗?”
那声音又来了。不是从耳中入,而是自骨髓深处渗出,像是另一个“他”在颅腔内低语。
于睿猛地睁开眼,抬手抚上眉心。指尖触到的是平滑肌肤,无痣。可越是如此,心中疑云越重:若我是逆种,那真正的主容器呢?是否早已葬身火海?而我这个“失败品”,竟因母亲一念之仁活了下来,并被误认为正统?
他忽然想起裴元启笔记中的字句:“双生子实验,主承命,逆试劫。”
一个承载天命,一个承受苦难。若命运可以转移,记忆能够篡改,那么所谓“我”,究竟是谁赋予的名字?
远处传来脚步声,轻而稳,是陈九娘。她披着素色斗篷,手中提一盏纸灯笼,光影摇曳映在雪地上,像一朵将熄未熄的莲。
“又做那个梦了?”她问,声音温柔却不容回避。
于睿点头,没有回头。“我在想,如果当年逃出来的孩子不是‘主容器’,而是‘逆种’呢?如果所有的一切??归心会、鸣心宴、祭忘台之战??都不过是一场错认身份的闹剧?”
陈九娘放下灯笼,走到他身旁,凝视铜钟。“那你现在是谁?”
“我不知道。”他苦笑,“但我知道一件事:无论我是主是逆,我都记得你教我识药时的手温,记得赵五为我挡刀时喷在我脸上的血,记得郑十三冒着杀头风险送来第一瓶醒神露……这些痛与暖,是真的。”
“那就够了。”她轻轻握住他的手,“人不是由出身定义的,是由选择决定的。你选择了唤醒别人,而不是控制他们;你选择了守住真相,哪怕它会撕裂你自己。这就足以证明,你是于睿,不是任何人的容器。”
于睿怔住,良久才低声说:“可若有一天,我的选择也不再属于我呢?当这东西彻底醒来,占据我的意识……我会不会亲手毁掉这一切?”
陈九娘沉默片刻,从怀中取出一枚小小的玉符,递给他。“这是堕云谷最后一只灵鼠临终前交给我的。它说,只有‘真正看见自己’的人才能启动它。”
玉符通体乳白,正面刻着一只睁目三眼的鼠,背面则是一行极细的小篆:**见我者,破梦。**
“什么意思?”于睿皱眉。
“意思是,当你终于敢直视镜中的自己,不论那里面藏着什么,你就能斩断最后一根操控之线。”她望着他,“但我不能替你完成这一步。必须是你自愿走进那个梦境,面对另一个‘你’。”
于睿握紧玉符,指节发白。
他知道,那一日终究要来。
三日后,朔月之夜,天地俱寂。于睿独坐归心堂密室,面前摆着三样东西:半瓶醒神露、灵鼠之血、玉符。他在案上写下遗书两封,一封给陈九娘,一封给天下。
>“若我未能归来,请继续开办学忆所,不要停。钟声可以断,但记忆不可灭。”
他将玉符置于额前,仰头饮尽混合药液。
剧痛瞬间炸开,如千针穿脑,万蚁噬心。他的身体抽搐着倒地,双眼翻白,口中溢出血沫。意识却被一股巨力拖入深渊??
眼前景象变幻,再度回到那间密室。
两具胚胎舱并列,玻璃罩内雾气氤氲。左边婴儿安睡,眉心一点朱砂痣;右边那个睁着眼,瞳孔漆黑如渊,正死死盯着镜头外的“我”。
画外音响起,苍老而冷酷:“第十七次抗性测试开始。注入高浓度梦引香。”
右边舱体猛然震荡,婴儿全身痉挛,喉咙里发出不成调的嘶吼。画面切换:铁笼、电击、幻象折磨……每一次失败,都被记录为“逆种缺陷”。而左边那个,则被抱出培养室,交予一名女子怀抱??那是母亲。
大火突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