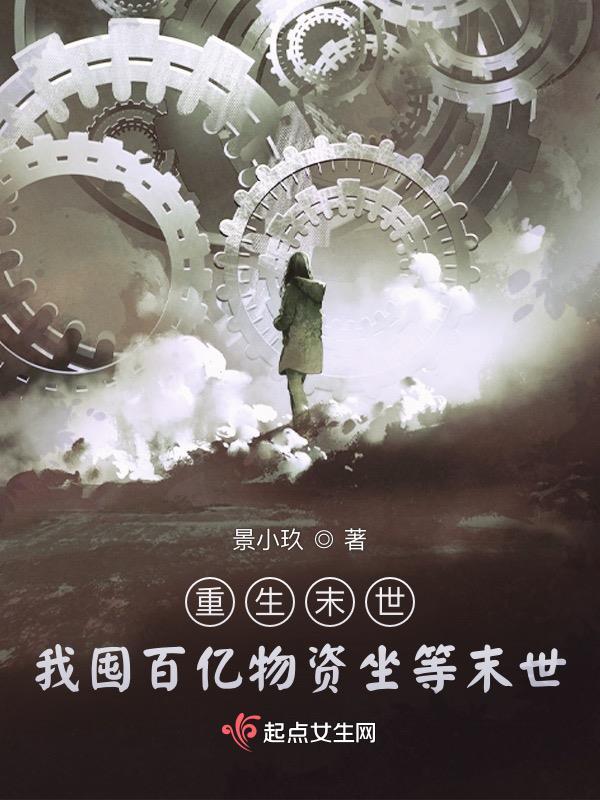BL小说>李珞应禅溪重燃青葱时代小说无防盗 > 第849章 你坏死了(第2页)
第849章 你坏死了(第2页)
学生们围坐成圆圈,听着袁婉青讲述云南孩子的故事。
当她展示那幅“画星星”
的素描时,全班陷入了短暂的寂静。
然后,李珞的儿子李晨举手了。
他是班里最沉默的男孩之一,从不主动发言,甚至连作业本上的字都写得极小,仿佛害怕被人看见。
“我……我也想写信。”
他的声音很轻,但足够清晰,“给我妈。”
教室里没人笑。
袁婉青只是温柔地看着他:“你想对妈妈说什么呢?”
李晨低头抠着桌角,许久才开口:“她去年走了。
车祸。
我爸说她是为救一只猫才冲出去的……我一直觉得,如果不是那只猫,她就不会死。
所以我恨那只猫,也恨我自己,因为我没拦住她。”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乎听不见。
但整个教室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袁婉青缓缓走到他身边,蹲下身,平视着他:“你知道吗?有时候爱就是这样,它不会计算值不值得,也不会等你准备好。
你妈妈冲出去那一刻,不是为了猫,是为了心里那个‘不能见生命消失’的自己。
就像你现在愿意说出这些,也是因为你心里还爱着她。”
李晨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他没有擦,任其滴落在膝盖上。
下课铃响后,他留在座位上,开始一笔一划地写信。
袁婉青走过时瞥见第一句:
**“妈妈,我现在不再骂那只猫了。
我想告诉你,我很想你,但我已经开始学着不躲起来哭了。”
**
那天中午,她在办公室接到一个陌生来电。
对方自称是周海生所在监狱的心理干预负责人,语气谨慎而尊重:“袁老师,周先生最近情绪稳定,积极参与改造项目。
他完成了您建议的‘亲子书信疗愈计划’,共抄写了87首林小雨的诗,并附上了他的反思日记。
我们考虑将这些资料作为减刑评估材料之一。
另外……他希望能见您一面,以家属心理咨询师的身份。”
她握着电话,久久未语。
窗外,紫藤花架上的枯枝似乎微微颤动了一下,像是回应某种遥远的召唤。
“我可以去。”
她最终说,“但不是作为家属咨询师,而是作为林小雨的同学、朋友,以及她没能等到的父亲的见证者。”
挂断电话后,她翻开抽屉,取出一本泛黄的旧相册。
那是她大学时期与林小雨的合影集。
照片里的女孩总躲在角落,笑容羞涩,眼神却清澈如泉。
最后一张拍于毕业前一周,林小雨站在图书馆台阶上,手里捧着一本诗集,风吹起她的发丝,她说:“婉青,你说以后会不会有人记得我写过的这些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