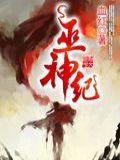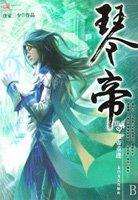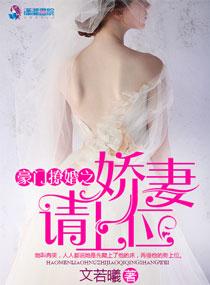BL小说>皇修萧舒TXT免费 > 第1221章 计划(第3页)
第1221章 计划(第3页)
最后一名高级特工被捕时,警方在他电脑中发现一段日记:
>“我们错了。
我们以为控制语言就能控制思想,却忘了思想本就不靠语言存活。
母亲哄睡婴儿的哼唱,恋人分别时的凝望,战士赴死前攥紧的遗书??这些都不是靠词汇完成的。
>我们摧毁了电台,封锁了书籍,禁用了方言,可我们堵不住人心想被听见的渴望。
>现在我坐在牢房里,隔壁囚犯不会说我的语言,但我们每天用手敲击墙壁,打同样的节拍。
>他说,那是自由。”
时代的潮水悄然转向。
联合国设立“沉默人权日”
,宣布“不被迫言说”
与“不被剥夺倾听”
同为基本权利;
脑机接口公司被迫公开源代码,“语言免疫协议”
成为全球公共财产;
曾经垄断全球信息流的科技巨头纷纷转型,其中一家更名为“根语集团”
,专研植物神经网络与人类语言的共鸣机制,声称已在玉米地中捕捉到类似克丘亚语的波动信号。
而在高原语塔第七层??宽恕之厅,每年都会迎来一批特殊访客:那些曾在“回音坟场”
效力的技术员、审查官、算法工程师。
他们不求赦免,只求能在墙上留下一句话。
有人写:“我曾删除十万条留言,如今只想听一句真话。”
有人画了个耳朵,下面写着:“请让它重新学会疼痛。”
最多的一句是:“对不起,我不知道那句话对你那么重要。”
陈砚偶尔会来这里走走。
他不再急于回应什么,只是静静地看,认真地听。
他知道,修复从未停止,也不会终结。
就像语言本身,永远处于生成与消亡的循环之中。
直到那个春日午后。
一个小男孩跑进无言学校,约莫七八岁,衣衫褴褛,眼神警惕如野猫。
他不会手语,也不愿触碰任何人。
整整五天,他不吃不喝,只盯着教室镜子发呆。
第六天清晨,陈砚走进教室,发现男孩正用指甲在镜面上划出几个歪斜汉字:
**他们烧了我的村子,因为我爸教人说老话。
**
陈砚蹲下身,拿起粉笔,在旁边写下:
**那你呢?你还记得吗?**
男孩摇头,泪水滑落。
陈砚轻轻握住他的手,带他走到庭院中那棵银叶槐下。
他指着一片新生的叶子,示意男孩触摸。
风起,叶响。
那一瞬,男孩浑身一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