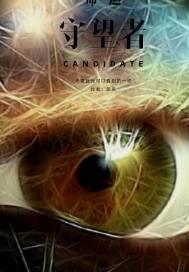BL小说>从盛夏到深秋 > 骤雨倾盆时(第2页)
骤雨倾盆时(第2页)
“老师!老师!”一个被狂风骤雨撕扯得断断续续、带着明显颤抖的声音,从下方艰难地传来。
是唐小棠。她穿着臃肿的明黄色雨衣,戴着大大的安全帽,正极其艰难地、一步一步扶着剧烈摇晃的脚手架梯子爬上来,怀里如同抱着珍宝般紧紧搂着一个用防水布层层包裹的记录板和笔。“陈…陈工让我来给您做现场记录!下面…下面所有人都等着您的数据呢!”
她的声音裹挟着巨大的风声雨声,充满了无法掩饰的紧张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对眼前这个冰冷专注身影的崇拜,更传递着下方那迫在眉睫、火烧眉毛的等待。风太大,雨太急,她爬得极其缓慢笨拙,雨衣的帽子被风掀起一角,露出同样被风雨打得湿透、冻得发红的脸颊和刘海。
林叙只是极快地、近乎冷漠地瞥了她一眼,又迅速扫了一眼下方如同在暴风雨中焦急等待蚁群般的人群,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似乎觉得多一个人上来完全是添乱和增加风险,但此刻分秒必争,根本顾不上多言,只从紧咬的牙关中挤出冰冷的一句:“跟紧!只记录数据!不准多话!不准干扰我!”他需要绝对的、不受任何干扰的专注。下方千百人的奋力拼搏,整个A7区的生死存亡,此刻都系于他手中仪器下一次的读数,系于他此刻的测量精度。
复核。必须精确到厘米。毫厘之差,可能满盘皆输。
他用冻得几乎完全僵硬、不听使唤的手指,艰难万分地操作着激光测距仪和地质罗盘,在狂风中竭力扭曲身体、寻找支点,以稳定自己,将仪器冰冷的镜头死死对准墙体上那些微小、只有他凭借经验和图纸才能精确辨识的标记点。数据在小小屏幕上剧烈地跳动、闪烁,每一次读数都无比艰难。
“点A1,X轴偏差:+2。3厘米,Y轴:-1。7厘米,高程:吻合!”林叙的声音在狂风暴雨中被撕扯、扭曲,却依旧努力保持着冰冷清晰的语调,每一个报出的数字都重若千钧,如同最终审判的落槌。
“收到!A1点,X+2。3,Y-1。7,高程OK!”唐小棠立刻用尽力气大声重复,手指冻得僵硬发紫,哆哆嗦嗦地在被风吹得疯狂翻卷、哗啦作响的记录板防水罩下,用力刻下每一个数字。
冰冷的雨水早已无情地顺着她的脖子、袖口往里灌,全身湿冷,但她死死咬着牙,努力让自己在摇晃的脚手架上保持平衡,全部注意力都紧紧聚焦在林叙的动作和他报出的每一个音符般的数字上。
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此刻记录的每一个数字,下一秒就可能转化为下方冲击钻启动的精确坐标,转化为灌浆枪瞄准的生死标靶!
啪嗒。
一滴冰冷彻骨、硕大的雨珠猝不及防地、重重砸在林叙握着测距仪的手背上,迅速洇开一片冰凉。他动作猛地一顿,心脏像是被那突如其来的冰冷触感激得骤然收紧,漏跳一拍。
他下意识地抬起头。
更多的雨滴,稀疏却沉重无比,如同断线的珠子,接连砸落下来,打在他冲锋衣的帽檐上、肩膀上,发出沉闷而令人心慌的“噗噗”声响。雨点迅速变得密集、急促,冰冷的雨丝开始无情地、斜斜地织入狂舞的风中,视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模糊、混沌。
雨水迅速浸湿了他的额发,一绺绺黏在额角,冰冷的水流顺着冰冷的脸颊滑落,洇湿了冲锋衣的领口,带来一片黏腻彻骨的冰凉。
但他只是猛地抬手,用早已湿透的袖子粗暴地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视线再次死死钉回那冰冷湿滑的墙体和手中跳跃的仪器屏幕上。
还有最后一个点!最关键的一个点!下面所有人都在等这最后一个点的数据!锚栓的最终定位、化学灌浆的精确开孔……所有的希望都悬于这最后一个坐标!
“老师!雨更大了!风也更猛了!这脚手架晃得厉害……我们……”唐小棠看着瞬间变得更加狂暴的雨势和脚下明显晃动加剧、发出不祥吱嘎声的脚手架,声音里充满了无法抑制的恐惧和担忧,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我们尽快!随时记录!”林叙头也不回地厉声打断,声音比这冰冷的雨水更加刺骨,带着一种不容置疑、近乎残忍的决绝。
误差必须控制在五厘米之内!这点雨……还不能阻止他!他死死咬着牙,强迫自己忽略湿透衣物紧贴皮肤带来的冰冷不适,忽略手指冻得几乎失去知觉的麻木刺痛,将最后残存的所有心神、所有意志,全部灌注于那即将完成的、关乎最终成败的测量上。
冰凉的雨水不断顺着他的下颌线滴落,砸在唐小棠手中记录板的防水布上,发出细微却惊心的声响,也重重砸在下方所有翘首以盼、心脏提到嗓子眼的抢险人员紧绷到极致的神经上。
……
云栖客栈,临时设备间兼指挥点。
狭小的空间里空气污浊不堪,弥漫着电子设备运行发出的低低嗡鸣声、纸张被频繁翻动的哗啦声、湿衣服散发出的潮气,以及一种几乎凝成实质、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的焦灼感。
沈佳宜正脸色发白地对照着复杂的手册,紧张地调试着多光谱和热红外设备,手指因为寒冷和紧张而不受控制地微微发抖。
陈工拿着对讲机,声音早已嘶哑不堪,却仍在对着另一头几乎是在吼叫,询问着防水布铺设的进度和困难。
沈知时,独自伫立在窗边,身影僵硬如同一尊被钉在地上的石像,与周围的忙碌嘈杂格格不入。
窗外,雨势正以一种毁灭性的速度疯狂加剧。豆大的雨点密集得如同瓢泼,疯狂砸在窗玻璃上,瞬间汇成一道道急促奔流的水瀑,将外面那个狂乱混沌的世界扭曲、模糊成一片不断晃动的、绝望的灰暗。
风声混合着震耳欲聋的雨声,如同万千失控的野兽在咆哮、嘶吼、撞击着一切。
他的目光死死钉在左手腕的表盘上。
秒针每一次冷静无情的跳动,都像一根冰冷的针,精准地扎在他早已绷紧到极限的神经末梢。十七分钟了。
从他眼睁睁看着林叙那道决绝的单薄身影消失在风雨中,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七分钟。这十七分钟,漫长得如同在炼狱中煎熬了十七个世纪。
腰间挂着的那个黑色对讲机,频道3的指示灯固执地散发着幽幽的绿色光芒,显示着连接从未中断。但紧贴耳边的听筒里,只有一片令人心胆俱裂的、单调而持续的无尽电流沙沙声。没有林叙清冷简洁的报数声,没有他压抑的呼吸声,甚至没有风声之外的任何背景杂音,只有这片吞噬一切的、死寂的沙沙声,如同最钝的刀子,在他心上一下下反复切割、研磨。
他无数次抬起右手,指尖悬在那个冰冷的通话键上方,塑料外壳早已被他掌心不断渗出的冷汗浸得湿滑黏腻。每一次,那个充斥着恐慌的念头都疯狂地冲撞着他摇摇欲坠的理智牢笼:呼叫!立刻呼叫!问他到哪里了?催他立刻回来!命令他回来!
但每一次,林叙冲出会议室前那冰冷抗拒得近乎厌恶的眼神、那句斩钉截铁的“别耽误时间”、那急于摆脱他一切关切的仓皇背影,都如同一堵无法逾越、寒气逼人的万丈冰墙,将他所有冲动的呼喊死死拦住,冻僵在原地。
他太了解林叙了。了解他的骄傲,他的固执,他那近乎自毁的责任感。此刻的任何呼叫,都只会被那个浑身竖满尖刺的人解读为干扰、不信任和多余的怜悯,只会刺激他在那危险至极的高墙上更加固执地证明自己,更加不顾一切地追逐那该死的厘米级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