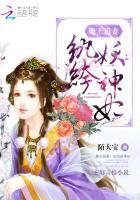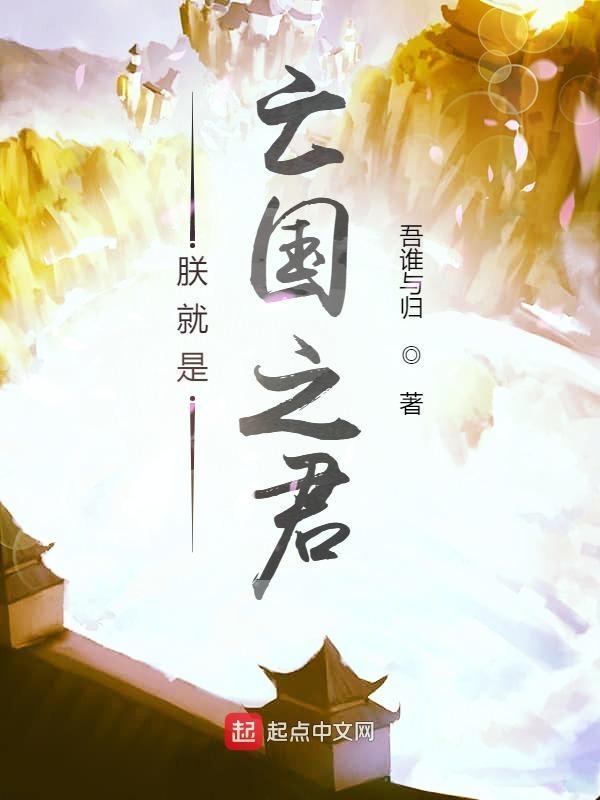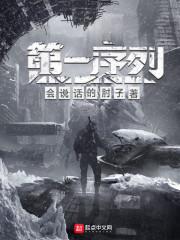BL小说>直男怎么冲喜? > 210220(第20页)
210220(第20页)
这次陈二顺也是来给父亲上坟的,自己没能给父亲送终成了他最大的遗憾。
大顺拍拍弟弟的肩膀,“爹知道您给东家效力,他不怪你,临终前还让我嘱咐你,好仆不侍二主,东家老太太、老爷和郎君都是顶好的人,待人和善宽容,你要好好在身边侍奉。”
陈二顺点头,他何尝不知道呢,如果当年没跟着老爷和郎君出来,自己也许还在陈家庄种地呢。
这些年他在府城见过了大世面,能在富贵人家里当管家是多荣耀的事。
晌午陈大顺在酒楼订了饭菜,以前清水镇是没有大酒楼的,只有几家小食肆做的饭菜味道也一般。
这家新开业的酒楼听说老板是从府城过来的,做的菜也都是冀州府那边的口味,味道吃起来不错。
吃完饭王瑛和陈青岩带着元宝回到熟悉的院子休息,元宝大了不能再跟他们睡一间屋子,王瑛把西屋收拾出来让他单独居住。
*
休息了一晚,第二日大家伙早早起来准备祭祀用的东西。
这次回去不光要祭祖,还要给青岩的父亲过六十生祭。
生祭也叫冥寿,在古代很讲究,需要提前准备三牲:即猪头、鱼和鸡,还有糕点、时令的瓜果、茶、酒等等。
除此之外,祭祀用的香烛和纸钱也必不可少,这些东西直接在香烛铺子里买现成的就行。
东西买完,马车浩浩荡荡的朝陈家庄驶去。
路上李氏和陈容、陈靖目不转睛的看着窗外,上了年纪回来一趟太麻烦,大概都知道这次能是最后一次回来了,下次再来怕是得等百年之后。
到了庄子上,这边比想象中发展的还要好。
家家户户都盖上了整齐的瓦房,虽然大部分村民还是以务农为生,但朝廷免去了税收,每年除了交一点粮食用来修祠堂外,其余的粮都归个人所有,只要手脚不懒日子过的都不会差。
听闻东家们回来了,大伙纷纷从家里出来,有个拄着拐杖满头白发的老妪,看见王瑛便要跪地磕头。
“可使不得啊!老人家这不是折我的寿吗?”
老太太咧嘴笑起来,露出参差不齐的几颗牙齿,“郎君还记得老太我吗?”
“记得,怎么会不记得,木头快过来看看李奶奶。”
站在陈泽身后的高挑青年走上前,“李奶奶好。”
“哎!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老太太拉着孩子的手上下打量,“真真出落成了人了,这下你爹娘爷奶也都放心了。”
当年她把木头送来的时候才八岁,如今一晃十年过去了。
春生也找到爹娘过去叙旧,许是离家太久跟家里人都有些生疏了,见了面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些年他没少往家里寄银子,询问爹娘有没有收到。
陈树根拘谨的点头,“收到了,家里盖房用的就是那个银子。”
“你跟娘照顾好身体,以后我再给你们寄银子。”
“不,不用寄了,你自己留着傍身,家里不愁吃喝。”
陈春生家里孩子多,他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下面还有几个姊妹,这么多孩子家里养不了才送过来,给孩子谋个出路。
如今见孩子出落的这么好,身上的衣服也干净体面,夫妻俩都放心了。
一行人步行朝祠堂走去,身后浩浩荡荡跟了一个村的人,还有不少其他村子闻讯赶来的人,都想一睹状元和进士老爷们的真容。
到了祠堂大门口,陈靖抬头看着高高的状元牌坊感叹道:“这牌坊真气派,花了不少工料吧?”
王瑛道:“县里安排的,请了六个木工师傅前后花了一个多月才做出来。”
陈大顺,随着沉重的大门打开,陈家祠堂映入眼帘。
陈靖是第一次过来,当他站在正堂看见父亲和母亲的牌位时,再也抑制不止眼里的泪水,掀起衣袍跪地道:“不孝子陈靖回来了,叩见列祖列宗!”
身后其他陈家的子嗣也同时跪地磕头。
穿堂风将他的发丝吹乱,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轻抚他的面颊,诉说着这些年的思念。
天气寒冷不能久跪,陈青岩和陈青淮上前把他扶起来,“四叔莫要难过,祖父祖母泉下有知我们这些孙儿这般争气,想来也是高兴的。”
陈靖拭了拭脸上的泪痕,“你说的对,他们一定会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