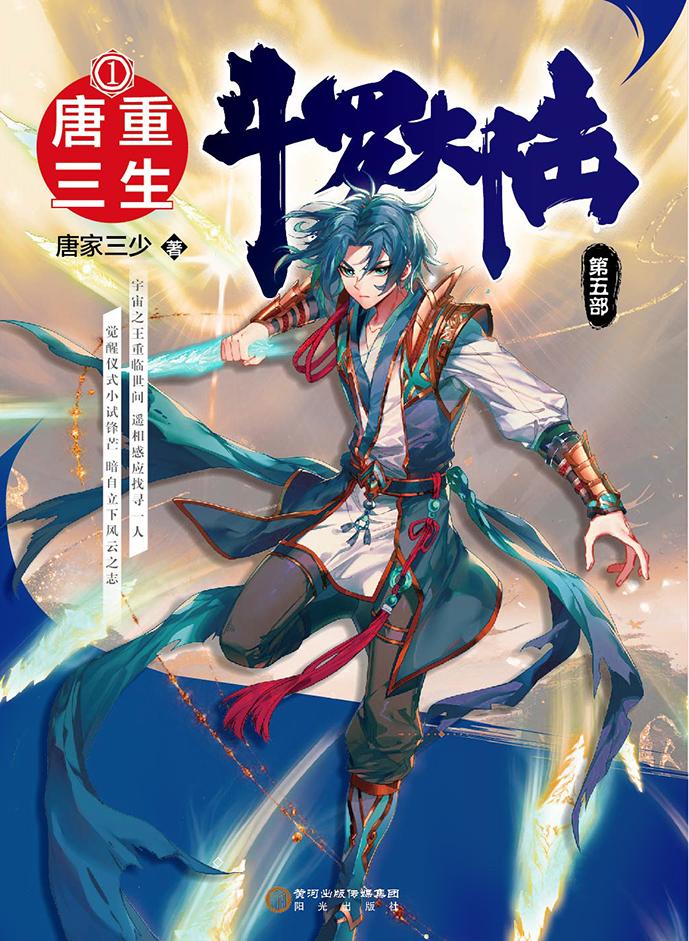BL小说>成了阴湿小狗的白月光 > 剑修卫让(第1页)
剑修卫让(第1页)
欧冶如槿先前已经不知被高家折磨了多久,哪里再禁得住这样的惊吓。她倒吸一口气,眼睛一翻,彻彻底底晕过去了。
她呼吸又轻又浅,如濒死之蝶轻轻翕动双翼。若不是白落烟知道她活着,恐怕会误以为她不在了。
卫让也是吓了一大跳,他忙伸手去探欧冶如槿的颈部脉络,而后才大松一口气。
“哎……”卫让摇摇头,不知地多少次叹气,有几分伯牙不见子期,曲高和寡的惋惜。又好像是带着重礼登门,但并未宾主尽欢的败兴。
他把剑挂回腰上,轻松把欧冶如槿扛到肩上,哼着不知名的小曲,慢悠悠往地宫外走。
白落烟默默跟在他身后,出石室的路上,不出意料见了满墙满地皆是喷溅的鲜红,和遍地横陈的尸体。那几个奉命看守欧冶如槿的恶仆,如今再没有嚣张模样,都横七竖八的倒在地上,颈子上一条刺目的血线。
白落烟重重叹口气,人死如灯灭,这一世善也好恶也罢,就此仓促结束了。
此时的高家一片死寂,如她与古神殿使者一起探访之时一般无二。这里已然没一个活物,连兽叫虫鸣都没有,说是鸡犬不留也不为过。
卫让却对阴森的气氛浑然不觉,他依然信步闲庭一般往院子深处慢慢走。
他走马观花,对满地狼藉东看一眼西看一眼,像是在逛自己宅子的后花园一般。
白落烟心底发寒,他的修为如此境界,理应可以用剑气快些离开这是非之地,可他并没有。
卫让有恃无恐,旁若无人般重回杀戮现场,分明是打算在走之前,再重新欣赏一次自己的满意作品。
没走多远,刚走到湖边桥上,欧冶如槿在颠簸中猛地醒来了。
她发疯一样挣扎,像一只发疯的猫,双手乱抓,尖锐的指甲在卫让脸上和脖子上划出几道长长血痕,触目惊心。
“哎,你……”卫让吃痛,但并未反击,显然是怕再给她添些新伤。他忙把欧冶如槿放到地上,一番混乱之中自己脸上脖子上倒是被她抓花了不少。
卫让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嘶一声,气笑了,“小姑奶奶,别看我副这德行,但我可是有家室的人!你这般无理取闹,叫我妻儿见了,定以为我怎么欺负你了!”
“你也有妻儿?那你怎么还这样……滥杀无辜……又怎能……怎能说是为了我才做如此恶行!”欧冶如槿瑟缩着往栏杆上靠去,指尖发抖。她又惧又矛盾,整个人都要碎了。
“我都说了我是个剑修啊,我哪里修习过怎么解灵咒?”卫让闻言用手背蹭蹭鼻子,没有对杀戮的悔恨,只有学艺不精的尴尬,“你这也太为难我了。”
他耸肩摊手,道:“再者说,我又不知道谁与你立的血契。这大半夜,我哪有功夫一个一个去查问?便是问了,他们也不一定讲真话啊。”
白落烟哑然,不得不说这卫让虽然残暴,但道理确实是这个道理。若真是查问,那不仅打草惊蛇,还未必问出什么真话。
“我不去,你也不是好人!我宁可死,也不给你铸剑!”欧冶如槿仍然十分坚持,纵然害怕,也不屈服。
“啧,我说小姑奶奶,你怎的如此不知变通?”卫让不耐烦地咂咂舌,“我赶时间,算我求你行不行?”
“多说无用,你杀了我吧!”欧冶如槿紧紧抱住身子发着抖,不知是害怕卫让还是高家,她声音不大,却十分坚决。
白落烟听了半晌,已然明白了大半,心头五味交杂。
事情有些不妙。
如槿虽说并非是蓄意为之,可与卫让的纠葛到底给高家带来了灭门之祸。
白玉京律令满是严刑峻法,哪里管你是无心还是有意?此事又涉及剑修与世家望族,为她脱罪谈何容易?
还没来得及想出办法,白落烟小腿上忽地一紧。
白落烟低头,只见几丝水草顺着池塘攀上她的腿,密密匝匝绕在她的脚踝上,想要将她无声无息拽进水里去。
儿时这件事白落烟此生都忘不掉。
这不知好歹的蠢货香炉!!都什么时候了,还偷偷摸摸耍花招!她几乎咬碎了牙,心里狠狠骂道。
水草骤然拉紧,白落烟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一回生二回熟,这次她有所防备,十指紧紧抓住了亭栏。
可她凡人血肉之躯哪里抵得过有灵力加持的水草,指甲在木栏杆上抓出了血也没有抓住,腰简直要被这股巨力扯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