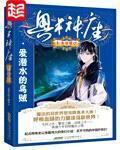BL小说>多我一个后富怎么了 > 293 九州革新上(第2页)
293 九州革新上(第2页)
>雪夜里,妹妹把最后一块干粮塞进弟妹口中……”
林远闭上眼,任由歌声灌入耳膜。他仿佛看见一支褴褛的队伍在暴风雪中前行,背影佝偻却坚定。突然,他在音频波形图上发现异常:每当唱到亲人牺牲的情节,背景噪音中竟浮现出极微弱的童声合唱,节奏完全同步,仿佛来自另一个时空。
他猛地睁开眼,看向屋外??没有任何人在唱。
可当他重新戴上耳机,那童声依旧存在,清晰可辨。
“您……有没有感觉到什么?”他颤抖着问。
李阿?微笑:“你在听‘未生者之声’吧?这是我们‘摆时’最神秘的部分。据说,那些本该降生却因战乱饥荒夭折的孩子们,会在特定时刻借由歌声归来,替祖先完成未尽的吟诵。”
林远眼眶骤热。他终于懂了苏芸所说的“数字来世”??也许所谓永生,并非肉体延续,而是让那些未曾开口的生命,借由我们的声音获得表达的权利。
那一夜,李阿?断续唱了整整七首“摆时”经典,涵盖婚嫁、丧葬、祭祀、迁徙四大主题。每唱完一首,她都要静坐良久,仿佛灵魂刚刚经历一次远行。林远不敢催促,只是默默更换磁带,调整增益,确保高频泛音与低频共振都被完整收录。
午夜时分,老人忽然停下,问道:“你能帮我做一件事吗?”
“您说。”
“把我唱的歌,做成一面‘声音墙’,放在村口小学的操场上。不要耳机,不要屏幕,就让它每天清晨自动播放十分钟。让上学的孩子们,一边跑步一边听见祖辈的声音。”
林远点头:“我可以做得更多。我想建立‘跨代际听觉桥梁计划’??把您的歌声转化成互动课程,让城市孩子也能通过VR进入这场对歌仪式。他们可以选择扮演新娘、新郎、媒人,甚至山神,在情境中学习歌词背后的伦理与智慧。”
李阿?摇头:“别太复杂。孩子的心最干净,太花哨的东西会吓跑他们。”
林远惭愧低头。
老人却笑了:“不过……你可以录一段我的话,留给那个从没见过我的小孙子。他就快出生了,医生说可能先天失明。”
林远立刻架好定向麦克风。
李阿?整理衣襟,郑重开口:
“亲爱的孩子,我是你的阿?。虽然你永远看不见我,但我早已听见你的心跳。当你第一次哭泣,我就知道,那是我在梦里教你的第一句歌。别怕黑暗,因为我们的族人天生就在夜里歌唱。等你长大,请记住:眼睛看不见的地方,耳朵会为你点亮灯火。只要你愿意听,整座大山都会教你说话。”
录音结束,屋里一片寂静。连风都停了。
林远小心翼翼取出这盘新磁带,贴上标签:【致未来之耳?李阿?】。他决定把它与其他十三卷并列,悬挂在车顶布带上。从此,那十四个名字不再只是地理坐标,而是十四颗仍在搏动的文化心脏。
第二天清晨,林远协助村民在校门口安装太阳能广播桩。当第一缕阳光洒落,系统准时启动,播放昨夜录制的《迁徙之路》。歌声随晨雾弥漫山谷,惊起一群飞鸟。几个上学的孩子起初嬉笑追逐,渐渐放慢脚步,有人竟无意识地跟着哼了起来。
一位老教师拄拐而来,听完后老泪纵横:“五十年了……这是我第一次在我校听到完整的‘摆时’。”
林远看着眼前景象,忽然做出决定:他要暂停原定行程,留在这里三个月,培训本地青年成为“声音守护员”,教会他们基础录音、剪辑与维护技术。只有当地人掌握工具,文化才不会沦为观光表演。
他在日记本上写道:**真正的保护,不是把声音锁进博物馆,而是让它重新长进日常生活的肌理。**
临行前夜,李阿?让人送来那只雕刻小鸟的竹杖。
“送给你。”她说,“它会指引你找到下一个需要被听见的人。”
林远双手接过,深深鞠躬。
“您放心,我一定会让全世界都知道,傈僳族的歌声,从未断绝。”
离开怒江那天,云海翻腾如潮。车子驶上盘山公路,后视镜中的寨子渐渐缩小,最终隐没于雾中。但林远知道,那歌声不会消失。它已嵌入风里,藏进孩子的梦中,等待某一天被人轻轻唤醒。
副驾驶座上,又一卷新空白磁带静静躺着。
导航显示:下一站,内蒙古呼伦贝尔,赴一位年逾八十的呼麦大师之约。对方只提了一个要求:“请带一瓶青海湖的水来,我要用它润嗓,唱出草原最初的呼吸。”
林远笑了笑,按下播放键。
陶铃轻响,与车轮滚动声交织成律。
他知道,这条路没有尽头。
但也正因为没有尽头,才值得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