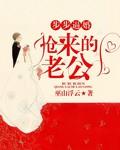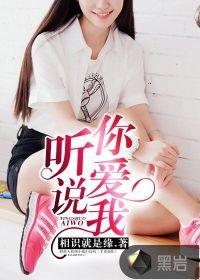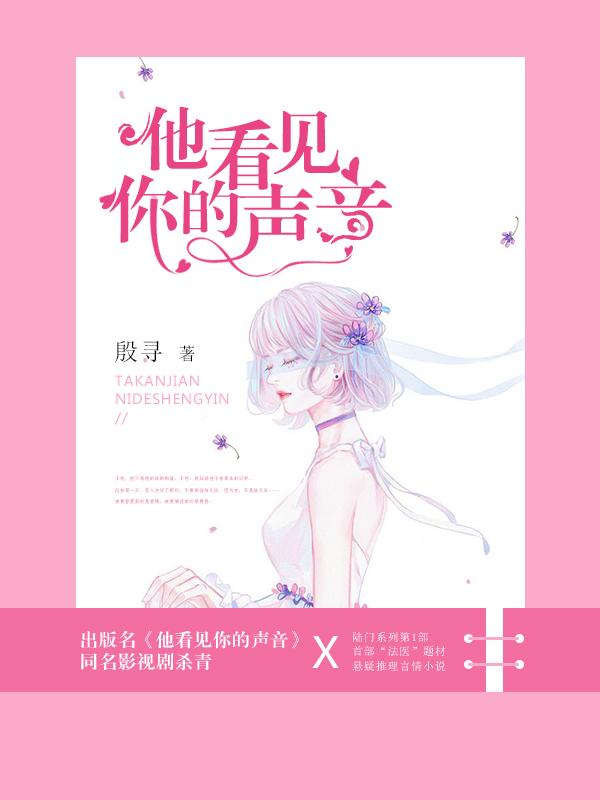BL小说>除却巫山不是云 > 第1章(第4页)
第1章(第4页)
我羞得赶紧低下头,接过江雪手中的同学录,又小心翼翼地放进书包里。
“那你记得明天给我啊!”
“嗯,好。”我边回答便抬起头时,只看到江雪飘然而去的背影。
晚上回到家里,写完作业后,我拿出江雪的同学录,轻轻地放在桌子上,小心地翻看。
我这才发现,她的同学录上也不过写了十来个人而已,我之前觉得很多人都写过可能真的只是我太心急的缘故。
我在空白的一页上填好自己的个人信息,有些得意地拿出草稿本,翻到最后一页,这是我早已准备好的给江雪同学录上写的内容。
接着,我认真地在这页写祝语的地方写道:相逢是首歌,同行是你和我,心儿是年轻的太阳,真诚也活泼。
相逢是首歌,歌手是你和我,心儿是永远的琴弦,坚定也执着。
是的,这是一首歌的歌词,歌名就叫《相逢是首歌》。
1997年的春天,央视八套播出了一部电视剧《红十字方队》,我很喜欢这部电视剧,让我憧憬了很久成为一名军队院校大学生的生活。
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就是《相逢是首歌》,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看电视的时候就经常跟着哼唱,等到电视剧演完也基本会唱了。
在看到江雪开始让人写同学录的时候,我就开始考虑要给她写些什么了。
同样这也不是因为我对她有什么特别的感情,而只是因为她太过优秀,我不想在她面前显得过于平庸。
写完后我又满意地看了一遍,比起那些“一帆风顺”、“祝你更上一层楼”
之类的俗套,我写的内容应该是颇为显眼了,而且这电视剧在当时的小学生里也没什么热度,想必江雪也没听过这歌,应该看不出这是歌词……
我心满意足地收起同学录,感觉终于完成了一件大事。
第二天来到学校,我拿着同学录走到江雪的桌子前递给她,说:“我写好了。”
“谢谢,谢谢啦……”江雪边说边接过去,坐在座位上翻开查看。
我便回到了自己的座位,我坐下时不禁又看了一眼江雪,发现她似乎是看完了我写的内容,正合上同学做出思索的样子,随后就转过头来看向我,正对上了我的目光,她马上露出那个当年拿走我手里的书时的笑容,我也有些害羞地冲她笑了笑,这便是我们在小学阶段最后的交流了。
当年没有什么小升初的择校,都是有什么学上什么学。
所以等到1998年的9月1日我仍旧像之前的每个开学报到的日子一样来到Y校时,发现班里的还是那些熟悉的面孔。
除了极个别人,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都选择继续在Y校上初中,当然也包括江雪。
在我来到Y校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了解到江雪其实也不是这个单位的子弟,她家住在和这个单位一墙之隔的一所大学里。
这所大学虽然只是个二本学校,但在当时是我们B市唯一的一所高校。
按理说江雪可以上她家院子里的子弟学校,没必要舍近求远地来Y校,虽然是一墙之隔,但两家的院子都挺大,又不能翻墙而过,从正门走的话还是颇有一段距离的。
而且当时还有个叫借读费的东西,去上这些人家单位自己办的学校都要交借读费。
不过初一报名这天的一个小风波,让我知道原来江雪是不用交借读费的。
报到那天,我们来到教室才发现教室里等着我们的是一张陌生的面孔。
虽然大家都知道初一肯定会换老师,但毕竟都在一个校园里,那几位初中老师也都早已经是我们见面问好的熟悉面孔了。
可没想到现在坐在教室里的这位板着脸孔的中年女人,是我们完全没见过的陌生人。
后来我们才知道,学校觉得我们这一级整体比较强,就专门给我们增强了师资的配备。
从市里其他的学校专门挖来了两位市级教学名师担任语文和数学老师,还让刚刚从初三下来的学校最好的英语老师给我们教英语。
现在坐在教室里的这位姓何的老师,就是我们未来三年的班主任,也是我们的数学老师。
何老师做完自我介绍,我们就开始排队缴费报到,一切都很顺利地进行着,直到轮到江雪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你不是子弟,怎么能不交借读费呢?”听到何老师疑惑的声音,排在队伍后面的我忍不住探头往前看。
“何老师,我一直都是不交借读费的……”江雪小心地回答。
“别人都交,为什么你不交?不交不能报名。”何老师很强硬,似乎还有些生气的样子。
“老师,我真的一直都不交的……”江雪的声音很委屈,她再优秀毕竟也只是个12岁的女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