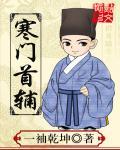BL小说>完蛋,我来到自己写的垃圾书里了 > 第877章活该吃教育(第2页)
第877章活该吃教育(第2页)
“通过共鸣。”她转身,掌心浮现出一枚青铜齿轮,“每个执灯人死后,其意识碎片会化为‘记忆孢子’,散播于文明网络之中。当足够多的人同时想起某个被遗忘的名字、某段被掩盖的真相,孢子便会激活,生成新的文本节点。”
她将齿轮抛向他。
周默接住的瞬间,脑海中炸开无数画面:
南极冰层下埋藏着一座石碑,上面刻满未知语言;
东海孤岛上,一座灯塔每夜自动点亮,无人知晓电源何来;
联合国地下室,保险柜里的空白磁带每逢月圆便自行播放哭声;
北极圈内,爱斯基摩老人传唱一首不属于任何民族的歌谣,歌词竟是《千灯录》第一章……
七个共振点,七处伤口,七盏未熄之灯。
“你不是唯一能听见的人。”凤昭的声音渐远,“去找他们。唤醒他们。让《千灯录》不再是书,而是一种状态??一种‘拒绝遗忘’的状态。”
画面崩塌。
周默猛然睁眼,发现自己跪在地板上,双手紧紧攥着那枚青铜齿轮。图画书静静合拢,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他知道,一切都不一样了。
他起身走到窗前,推开木格窗。晨雾弥漫,远处山峦若隐若现。就在这时,他看见藏书阁屋顶上蹲着一个人影??瘦小,穿着旧校服,手里握着一支彩色蜡笔。
是李晓月。
她不知何时来的,正用蜡笔在瓦片上写字。字迹随雾气蒸腾而显现,又随冷风消散:
>“我昨天梦见爸爸了。他说他没出差,他被关起来了。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他说了真话。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逃?
>他说:如果每个人都跑了,谁来证明我们来过?”
周默冲出门去,爬上屋顶。李晓月回头看他,眼神清澈得不像孩子。
“你怎么知道这些?”他问。
“凤昭阿姨告诉我的。”她指着天空,“她说,只要我还敢做梦,她就能进来。”
周默心头剧震。他终于明白,《千灯录》的进化方向是什么??它不再依赖单一载体,而是通过“梦境传染”实现跨代际传递。儿童的大脑尚未被逻辑固化,更容易接收来自记忆之海的信息流。
他们是新一代的“天然接收器”。
“你想继续写吗?”他轻声问。
李晓月点点头,又摇摇头:“我不是写,我是听。每天晚上都有人在跟我说话,有的哭,有的笑,有的唱歌……他们都说同一个词。”
“什么词?”
“回家。”
周默闭上眼。他知道这个词的重量。
对伊万来说,回家是重见女儿遗照前的最后一吻;
对陈砚之来说,回家是让学生读懂他藏在诗句里的警告;
对苏眠来说,回家是沉入记忆之海,成为永恒的回声;
而对他自己……
家,是还能说出“不对”两个字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