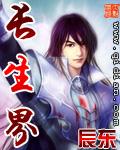BL小说>带着玩家在大唐搞基建的日子 > 250260(第27页)
250260(第27页)
当然不会有人站出来。
“很好,看来没有。你们每个月领着俸禄、谏纸,享受朝廷种种优待,希望以后不要再让我看到这种浪费笔墨纸张的东西,好吗?”
骂完了人,雁来的心情总算好了一些,又道,“对了,你们交上来的策论我已经看完了。正好今日大家都在,就在这里公布结果吧,谁有异议也可以当面提出,把你的文章找出来公议。若是现在不说,回去又编排什么,那就只能依律处置了。”
她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递给李绛,这才重新坐了下来,面无表情地听着李绛宣读文件。
下面很快骚动起来,因为第一段就是总结,不合格的文章比预想的更多,占了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而且后面立刻就说了,不合格者,甚至都不会被贬官外任,而是直接革职回家!
这在大唐是很少见的。京官最常见的处罚,就是贬到外地去做官,罪轻的就去好一点的地方,罪重的就流放岭南、广西、贵州那些偏远蛮荒之地,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的身份依旧是官员,还有遇赦回朝的指望。
革职回家听起来没那么严重,却等于是彻底断送了仕途。
第258章你好歹装一下啊!
大唐开国近二百年,单是最受重视、录取人数也最少的进士科,也有超五千人通过考试,更不用说还有其他明经、明法等录取率更高的科目了,而且每一年都在源源不断录取更多的举子。
另外,大唐还有一半的官员是以门荫入仕。
如此一来,仅仅只是整个文官集团规模,就已经庞大到不可想象了。
为了安置这么多人,大唐的冗官才会越来越多,每年光是给官员发俸禄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即便如此,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官做。
有人因为丁忧等原因暂时离职,回来就要重新排队选官,有人对官职不满意,辞职之后就一直赋闲,甚至还有人进士及第,却一直没能选上官,等待时间最长的人,据说做了二十年前进士。
——大唐的进士指的是各地解送进京参加考试的士子,等同于宋以后的举人,而非进士。时下也没有考中进士的说法,而是说进士及第。进士们解送入京时,会在各地驿馆题诗留名,及第之后便加上一个“前”字。因此也就将尚未通过吏部铨选、释褐为官者称为“前进士”,有点类似现代的博士后,有文凭没职务。
有这么多人在排队守选、等着补一个官缺,他们一旦被革职回家,几乎不可能再回到朝中。
除非换一个当政的人。
可是雁来今年才不到二十岁,在场这些人能熬死她的几率实在不大。
所以被宣告不合格者,心中的绝望可想而知——他们既是谏官、又是近臣,本来是整个大唐最有前途的一批官员,却一朝化为乌有。
不合格者失魂落魄,顾不上提出异议,合格者自然更不会有异议了。
但雁来想了想,还是让人找出了他们的文章发下去。也让他们看看,这可不是她公报私仇,而是文章确实写得不行,她顶多只是用红笔将写得不行的地方都划出来,写上了评语。
没错,就像是老师阅卷那样。
水平越差,红色越多,一目了然,自己都不好意思赖着不走。
自己想说的都说完了,见他们没有什么话要说,雁来便摆摆手,让人退下。
弹劾的事,水面上的部分应该就到此为止了——所以说为什么非要让她走个流程呢?最后倒霉的又不会是她——至于水面下的部分,得等俱文珍那边的进展。
不过有名单在手,察事院要做的不过是一些跑腿问话的事,倒也简单。
又过了一天,雁来就拿到了更加详细的资料,不仅按照她的要求列出了各人所犯的罪行,还记录了他们这一回串联起来的原因。
其实也没什么新意。
雁来自认为给每一个群体都留下了出路,只要他们肯主动去适应新环境,就算不能过得更好,也不会比之前更差。
但他们过去侥幸获得了与自身实力不匹配的好处,便以为是理所当然了,如今或是固守陈规、畏惧改变,或是认为新获得的利益不如自己想要的多,又或是只愿坐享其成,等她将好处强塞进他们手里……
总之,就是对现状不满意。
不满意,就是她的错。
雁来甚至都懒得为了他们再将朝臣叫过来走一遍流程了。
这些人之所以到现在还执迷不悟,一方面是天资有限,难以跟上瞬息万变的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距离雁来、距离朝廷、距离大唐的政治中心都挺远的,所以根本看不清朝中大势。
既然如此,也没必要处理得大张旗鼓。
雁来将名单还给俱文珍,“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走正常的流程就行。”
“是。”俱文珍应下,面上露出一点欲言又止的神色。
像他这样的老人,当然不会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做出这种表情,就是等着她去问。
雁来也就问了,“什么事?”
“那篇文章……”俱文珍说,“情况比预想的复杂一些,不过人已经找到了,殿下可是现在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