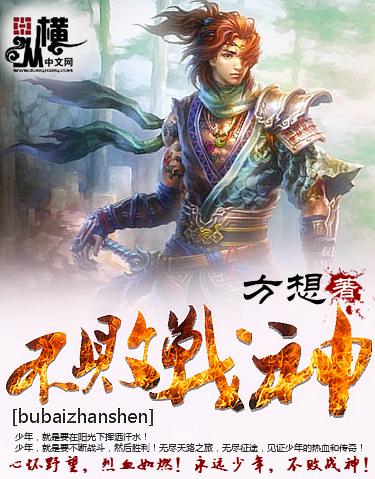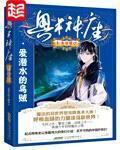BL小说>娱乐:全网黑的我,被中科院连夜捞走 > 第171章 带你去见一个人(第3页)
第171章 带你去见一个人(第3页)
“那时刚从国外引进第一批实验设备,我带着团队偷偷做过几轮模拟推演。”
他抬手比划着,骨节嶙峋的手指在空中勾勒出抽象的图形。
“你看这些数据,是关于材料在量子纠缠态下的能量转换模型。”
“可惜啊,当时主流学界都在攻纳米涂层技术,项目连立项资格都没有。”
老人咳嗽几声,颤巍巍地指着笔记本某一页。
“这组公式,是我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硬啃出来的。”
“记得那年冬天,整个实验室的暖气都停了,手冻得握不住笔。”
他的声音渐渐低下去,像是沉入了回忆的深海。
“后来项目被叫停,设备被调去支援其他课题。”
“但我总觉得,这东西迟早会派上用场。”
他重新看向楚衍,浑浊的眼睛里突然亮起光。
楚衍的手指死死扣住笔记本边缘。
仿佛触到了某种跨越时空的震颤。
沈骁的推演,无异于19世纪的航海家在没有卫星地图的年代。
仅凭季风与星轨,就标注出了新大陆的坐标。
他忽然想起幼年时听过的故事。
二十世纪初,一位乡村教师在煤油灯下计算铁路弯道弧度。
而当时他的村庄连汽车都未曾见过。
又如敦煌藏经洞的守护者,在战火纷飞中用毛笔逐字抄录经文。
那时没人知道千年后这些文字会成为解读文明的密钥。
沈骁的研究同样如此。
当整个学界还在传统材料的迷宫里徘徊。
他却像个预知未来的画师。
在空白画布上勾勒出尚未成型的图景。
这种超越时代的洞察力。
像明代万户将火箭绑在椅子上的惊世一跃。
明知可能粉身碎骨。
却依然选择向未知的苍穹伸手。
沈骁在没有任何实验数据支撑的岁月里。
仅凭理论推演便触及材料学的未来边界。
这需要的不仅是深厚的学术功底。
更是一种近乎偏执的直觉和勇气。
笔记本里的公式在楚衍眼中突然鲜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