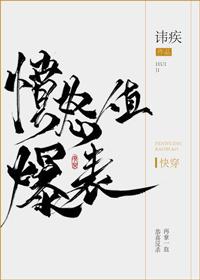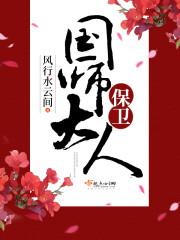BL小说>铸命成剑,斩魂登仙 > 第三百四十八章 剑匣晋升 化身晋升(第4页)
第三百四十八章 剑匣晋升 化身晋升(第4页)
谢无咎释然一笑。
他盘坐于虚无之中,双手结印,将体内残存的问种之力尽数释放。光芒如丝,缠绕镜身,镜面渐渐透明,映出万千世界:有的城邦以逻辑为法,人人理性至极却再无笑声;有的国度奉情感为神,爱恨交织成灾;还有一界,所有人共享思维,个体意识早已消亡……
每一界,都曾源于一个美好的问题,最终却陷入新的极端。
“没有完美的答案。”他喃喃道,“只有不断重问的勇气。”
镜碎。
他醒来,已在山巅之外,漂浮于虚空。
脚下昆仑渐远,地上人间如棋局展开。他看见北方草原的孩子点燃新篝火,南方海岛的渔夫对着潮汐发问,西域沙漠中的旅人用沙画记录疑惑……无数微光在大地上闪烁,如同新生的星群。
他知道,那便是散落四方的问种之光。
十二道星线并未消失,而是深入民间,化作平凡人的顿悟瞬间:农妇在喂鸡时突然想到“平等是否需要条件”,铁匠打铁间隙喃喃自语“规则该不该有例外”,书童抄书至深夜,提笔写下“如果真理让人痛苦,还要追求吗”。
这些光,不再集中,不再显赫,却更加坚韧。
他不再下降。
身体逐渐透明,与风融为一体。衣袍飘散成絮,化作云霞;骨骼轻鸣,转为清音;最后连意识也如露水蒸发,融入天地间的疑问之流。
世人称那一日为“谢逝”。
但三年后的某个春夜,西北戈壁一场沙暴过后,枯槐旧址竟长出新芽。牧羊少年在其下歇息,忽觉脑中浮现一问:
>“既然一切皆可质疑,那‘质疑’本身呢?”
他惊愕抬头,只见风中似有一道模糊身影微笑颔首,随即消散。
而在东海之滨,苏明璃授课归来,发现窗台上多了一片焦黄的纸屑,边缘蜷曲如火灼,中央却完好无损,写着一行熟悉笔迹:
>“不必找我。
>我正在每一个不肯闭嘴的灵魂里。”
她泪流满面,将纸片夹入《逆命录》最后一章。
多年后,有学者整理古籍,发现原本空白的末页,不知何时浮现一行小字:
>“命不可铸剑,唯志可成锋。
>魂不必斩尽,但疑须长存。
>登仙路远,不过一步一问。”
书传天下,无人知作者是谁。
唯有每月十五,昆仑绝顶的石碑会自行亮起一刻钟,碑面变幻不定,有时是“你是谁”,有时是“你怕什么”,有时只是一个简单的“?”。
据说,若有纯粹之心者立于碑前,白焰会轻轻跃动,仿佛在回应。
而每当夜深人静,风掠过山川河流,穿过市井巷陌,总有人忽然停步,仰望星空,喃喃道出一句无人能解的疑问。
那一刻,他们的瞳孔深处,会闪过一丝银光。
如同曾经的谢无咎。
如同永不停息的问种。
如同,斩断愚妄、照亮长夜的??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