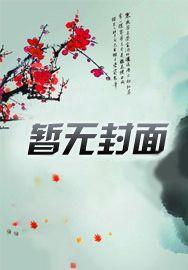BL小说>都重生了,谁还当演员 > 第781章 先下手为强(第2页)
第781章 先下手为强(第2页)
>“山很高,路很远,
>我的脚步很小很小。
>可我的声音,想飞过垭口,
>落在你不曾看见的桥。
>
>风来了,我不躲,
>雨打了,我不缩。
>因为我知道,
>总有人在等这一首歌。”
歌声并不完美,有几个音跑了调,但她一直坚持到最后一个字。当最后一个音符消散在晚风中,整座山谷仿佛都静了下来。
三秒钟后,远处传来一声清脆的回应??那是邻村学校的广播喇叭,正在重播这段录音。
紧接着,第二声、第三声……七个村落的广播系统依次响起,同一首歌在群山之间来回传递,如同星火燎原。
杨蜜打开后台监控,数据显示:这条音频在十五分钟内被转发一万三千次,收听人数突破八十万。有网友留言:“这是我听过最干净的歌声,没有修音,没有包装,只有真实的心跳。”
更令人震惊的是,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怒江籍男子连夜驱车一千公里赶回家乡。他在社交媒体写下:“我三十年没回过村子,因为我恨这里穷、闭塞、让人抬不起头。可昨晚我听见女儿唱歌,才明白我逃开的不是贫穷,而是害怕听见自己的根。”
他捐出全部积蓄,用于扩建村小的声音实验室,并承诺每年暑假回来做志愿讲师。
一个月后,“声音接力站”扩展至全国三十二个偏远地区。西藏牧区的孩子开始用藏语录制睡前故事,内蒙古草原上的少年把马头琴声与心事一同封存进音频胶囊,广西瑶寨的老人们教会孙子孙女如何用古谣传递思念。
而这一切的背后,一场看不见的连锁反应正在发酵。
某天,杨蜜接到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电话。对方语气郑重:“我们准备将‘倾听能力评估’纳入中小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体系。不是考他们说了多少,而是考他们是否学会听完别人最后一句话。”
她握着电话,一时说不出话。
挂断后,她翻开最新的项目报告,看到一组数据让她怔住:
-全国已有四百七十六所学校设立“沉默时间”课程,每天预留十分钟让学生自由录音;
-“听见计划”合作医院的心理危机干预成功率提升至82%,其中73%的患者表示,“第一次觉得有人真的在听我说话””;
-更有两名曾参与项目的聋哑儿童家庭,借助语音重建技术,实现了人生首次“对话”??母亲含泪录下二十年未说出口的“对不起”,儿子则用手语配合AI翻译回应:“妈妈,我现在听见了。”
春天转入初夏,北京郊外的一家安宁疗护中心迎来特殊访客。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躺在病床上,呼吸微弱。他是中国最早研究儿童语言发展的学者之一,晚年罹患渐冻症,全身肌肉逐渐失去控制,唯独声带尚存一丝力量。
“我想……留下最后一课。”他对前来探望的杨蜜说。
于是,在那个蝉鸣阵阵的午后,一间小小的病房变成了课堂。二十名“声音疗愈师”围坐一圈,戴着耳机,屏息凝神。
老人用尽力气开口:
>“人类最原始的连接,不是文字,不是图像,而是声音。
>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母亲就会冲过去;
>孩子喊出第一个‘妈妈’,全家都会落泪。
>可我们长大后,却把声音变成工具??命令、指责、炫耀、掩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