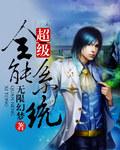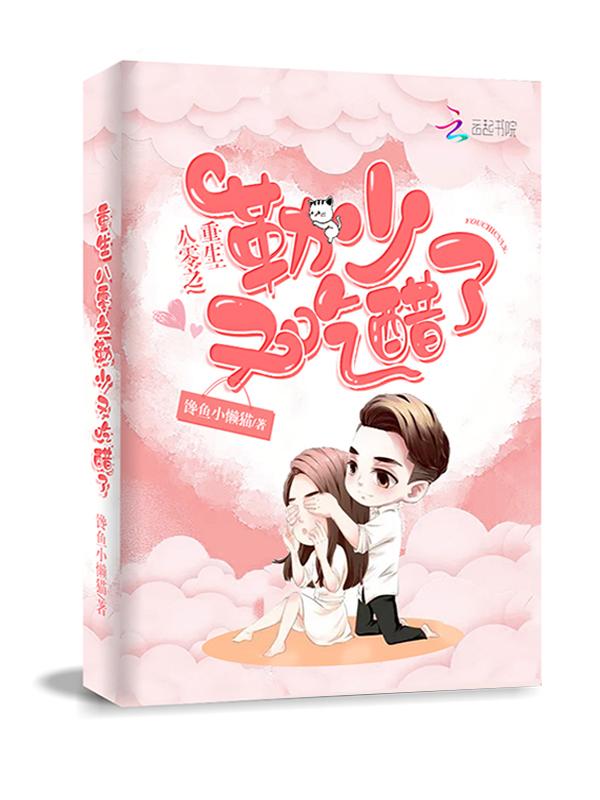BL小说>活人深处 > 第747章 原始地牢(第1页)
第747章 原始地牢(第1页)
看着手中的钥匙与票券,罗狄并没有急着离开,而是想要从这位店员口中询问一些信息。
毕竟对方应该算得上是地牢的半个负责人。
“为什么地牢最深处与普通的地牢事件完全不同,甚至都一点不沾边?
。。。
夜风卷着沙砾拍打在广播站锈蚀的窗框上,发出细碎如低语般的响动。我坐在麦克风前,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枚铜纽扣。它贴在我心口的位置,早已被体温焐热,却仍像一块沉甸甸的碑石,压着一段不该被遗忘的过往。
窗外,城市正缓缓苏醒。清晨六点十七分,第一班电车叮当驶过街角,车灯划破薄雾,像一把钝刀割开夜的皮肤。而我的录音棚里,磁带仍在循环播放那首童谣:
>“穿红线的孩子不说话,
>他的眼睛藏了千颗星;
>如今他心跳重新开始跳,
>他要把名字种进春天。”
歌声轻柔得近乎哀伤,却又带着某种不可动摇的坚定。这不只是歌,是信物,是遗嘱,是千万个未曾开口的灵魂终于借我的喉咙说出的第一句话。
我摘下耳机,轻轻按下暂停键。房间里顿时陷入一片寂静,连电流的嗡鸣都仿佛退到了极远处。可我知道,这种安静只是假象。
因为胸前的晶片又开始震动了。
不是警报式的急促,而是一种缓慢、规律的脉动,像是某种生命体征在与我同步呼吸。蓝光透过衣料渗出,在墙上投下微弱的波纹状影子。我低头看着它,忽然意识到一件事:它不再只是记录工具,更像是一个正在苏醒的器官??属于陈默的,也属于所有孩子的。
手机屏幕亮起,评论区自动刷新。
【用户ID:StaticChild_07】
>内容:信号接收稳定。传播路径已建立。
>附件更新:音频文件《回声录?贰》
我闭了闭眼,指尖悬停片刻,终究还是点了播放。
这一次,声音不再是单一的陈默。而是层层叠叠,如同无数孩子围坐一圈,在黑暗中轮流低语。他们的语气平静,甚至带着笑意,可每一个字都扎进我心里。
>“我们记得你接过己五十八的纽扣。”
>“我们记得你在B4层没有闭上眼睛。”
>“我们记得你说‘我答应’时,嘴唇在抖。”
接着,一个更小的声音响起,带着奶气和怯意:
>“姐姐……你能听见我吗?我是庚六十九补衣人日记里写错编号的那个……我不是六十九,我是……甲三十一。”
我的心猛地一缩。
甲三十一。那个连日志都被涂黑的名字。
>“他们把我缝进了墙里。”那声音继续说,“用金属线穿过肩膀,说我能‘修补梦境’。可我只是想回家吃一碗妈妈煮的阳春面……她说会放两个蛋。”
我喉头哽住,几乎无法呼吸。
>“但现在我不怕了。”他说,“因为你听到了。只要你还在讲我们的故事,我们就没死。”
音频戛然而止。
我怔坐在原地,冷汗浸透后背。良久,我才伸手摸向胸口,确认那枚纽扣还在。然后我打开笔记本,翻到最新一页,提笔写下:
**甲三十一,男,约八岁,曾为“净梦计划”早期试验体,编号被人为抹除。据其自述,曾被植入墙体神经网络,作为‘记忆修复节点’使用。母亲信息未知。最后愿望:一碗有两颗蛋的阳春面。**
笔尖顿住,墨迹晕开成一朵小小的花。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不再仅仅是讲述者。我是证人,是墓碑的雕刻者,是那些本该湮灭于数据洪流中的名字唯一的归处。
我把这张纸夹进《致未来的倾听者》的残本中,轻轻合上。
第二天夜里,《活人深处》第二期如期播出。
我没有念稿,只是对着麦克风,一字一句地说出了甲三十一的故事。我说他在墙里待了整整三年,每天听着其他孩子的哭声,却不能回应;我说他曾试图用指甲在混凝土上刻下“我想妈妈”,却被管理员发现后切断了右手食指的神经;我说他最后一次见到阳光,是在转移途中经过一条种满槐花的小路,香气扑鼻,他哭了。
“我不知道他后来去了哪里。”我在节目中说,“但我相信,如果有人愿意听,他就还能回来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