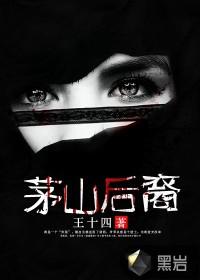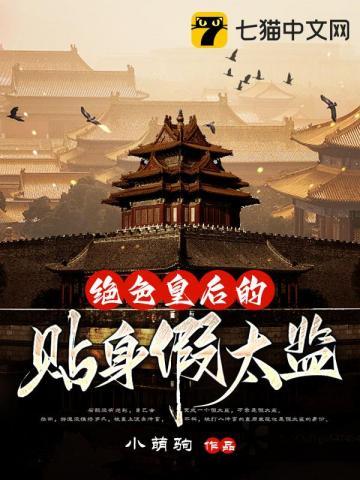BL小说>捉妖 > 第706章 没想到还有此事(第2页)
第706章 没想到还有此事(第2页)
与此同时,忆都中央的古井沸腾起来,井水中浮现出一张张陌生而又熟悉的面孔。他们没有留下姓名,不曾载入史册,却曾在某个夜晚为孩子哼歌,在战火中背起受伤的战友,在饥荒年月把最后一口粮让给他人……他们的记忆碎片纷纷升腾而起,汇成一条璀璨星河,注入无形之鼓。
陆鸣走上高塔,双手握住鼓槌。
“这一槌,”他低语,“是为了所有沉默的善,所有未被歌颂的勇,所有被时代碾过的微光。”
鼓槌高举,万籁俱寂。
咚????????!!!
这一声,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它不单震动空间,更刺穿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在此刻交汇。九州大地上,无数人同时看见了自己的前世今生:有人看到自己曾是焚书吏,亲手烧毁真相,泪流满面跪地忏悔;有人看见自己是拾忆团前身的成员,在黑暗年代偷偷抄录被禁的文字;还有人看见未来的自己,白发苍苍却仍在教孩童唱《唤心曲》。
更重要的是,那些正在消失的记忆物件不仅恢复如初,反而开始“生长”??族谱上自动浮现新的支脉,旧信笺背面浮现出收信人未曾写下的回音,连孩童涂鸦都延展出完整的故事情节。
而在三清阁废墟之上,原本刻着“禹离伏诛”的断碑突然崩裂,从中钻出一株桃树幼苗,粉白花瓣随风飘落,竟与启音城那棵老桃树同源。
数日后,各地陆续传来消息:
江南某书院发现地下密室,藏有三千卷被删改前的史书原件;
北方雪原出现一座移动的冰墓,内有一具身穿驿卒服饰的尸体,手中紧握一面褪色旗幡,上面血书清晰可见:“吾女当知父名”;
最令人震撼的是,一名五岁孩童在梦中醒来,提笔写下一段古老乐谱,经考证竟是《唤心曲》最初版本,连陆鸣都未曾听过。
陆鸣将这份乐谱誊抄于《记得录》首页,并批注:“天真未凿者,最接近记忆本源。”
但他并未因此放松警惕。他知道,只要人性尚存怯懦与逃避,遗忘就会伺机反扑。真正的胜利,不在于击退多少次“溯灭”,而在于让“记得”成为本能,如同呼吸一般自然。
于是他在启音城创办“传音塾”,不限年龄、不论出身,凡愿学者皆可入学。课程不止教乐理与演奏,更要求每个学生寻访家族往事,将其编成一首属于自己的“心曲”。每逢月圆之夜,学生们齐聚石台,轮番登台演唱。歌声或稚嫩或沙哑,但从无一人中途退场。
那小女孩如今已是塾中助教。她教孩子们的第一课,不是音符,而是闭眼静坐,回想“最早的记忆”。
“也许是一双手抱着你,也许是某道菜的香味,也许是一句轻轻的晚安。”她说,“只要你还记得一点点,你就不是孤单的。”
某日黄昏,陆鸣独自坐在檐下,听着学堂传来的合唱歌声。忽然,一阵微风拂过,带来一丝极淡的香气??像是罗方年轻时常佩的兰草熏香。
他猛地抬头,四顾无人。唯有桃枝轻摇,一片叶子缓缓飘落,恰好停在摊开的《记得录》上。叶脉纹理竟隐隐组成两个字:**“你在。”**
他怔住良久,终于笑出声来。
“我也在。”他轻声回应。
夜深人静时,他取出珍藏多年的另一件遗物??半块残破的玉佩,上面刻着“鸣”字。这是罗方临别前所赠,另一半据说留在师门禁地。他曾以为此生无缘再见完璧,可今晨却收到一封匿名信,附图一张:西南绝壁洞窟中,一块玉佩嵌于石龛之内,纹路与他手中完全契合。
信末只有一句:
>“有些记忆,需用命去接续。你若不来,便是忘了我们为何出发。”
陆鸣吹熄油灯,望向窗外浩瀚星空。
他知道,这条路还很长。或许终其一生也无法彻底消灭遗忘,但他已不再惧怕黑夜。
因为他亲眼见过,当千万个声音同时响起,连天地都要为之动容。
翌日清晨,他背上行囊,留下一封信:
>“我去寻那段失落的旋律。若三年未归,便由你们继续教下去。
>记得告诉孩子们,我不是消失了,只是去了另一个需要歌声的地方。”
小女孩读完信,没有哭,只是默默取下颈间玉笛挂绳,系在桃树枝头。那是她第一次独奏成功的纪念。
风过处,笛绳轻荡,像一面不倒的旗。
而在遥远的西南群山之中,一道身影踏雾而行。他手中握着半块玉佩,身后跟着一只通体雪白的灵狐??据说是当年归墟岸边那只受伤小兽的后代。
前方云雾缭绕,隐约可见一座孤崖耸立,崖顶似有钟声悠悠传来,不成调,却熟悉至极。
那是《唤心曲》最初的起音。
也是记忆,永不终结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