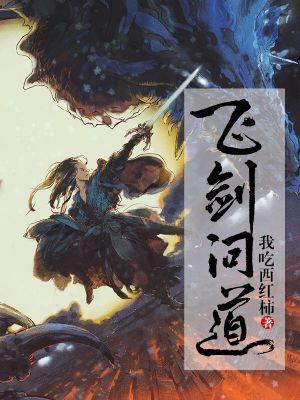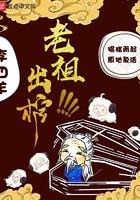BL小说>这个导演睚眦必报 > 第589章 姐姐们隐身的第30天我怀念她们(第2页)
第589章 姐姐们隐身的第30天我怀念她们(第2页)
“我是特种兵出身,参加过维和任务。回国后娶了家乡姑娘,本以为能安稳过日子。可婚后第五年,她开始怀疑我出轨。没有证据,但她每天搜我手机,监听通话,甚至在我执勤时跟踪到部队门口大闹。”
“我不敢还手,怕被人说‘打女人’。可她越来越极端,有一次拿开水泼我胸口,还笑着说‘看你还能不能逞英雄’。”
镜头切到医院病历:二度烫伤,住院十七天。
“最痛的不是皮肉,是心。”他说,“战友来看我,问我怎么搞成这样。我说骑车摔的。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被打成了懦夫。”
视频最后,他站在军营旧址前敬礼:“我不是来博同情的。我只是想告诉所有还在忍的男人:你可以坚强,也可以哭。你可以保卫国家,也应该保护自己。”
这条视频二十四小时内播放量破亿,微博话题#退伍军人自述被家暴#爆火。无数男性留言:“我也是”“我一直不敢说”“原来我不是怪物”。
与此同时,基金会公布的第二批127例真实案例档案引发学界关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公开发文称:“长期以来,我国反家暴研究存在‘性别盲区’,默认受害者=女性,施暴者=男性。这种刻板印象导致大量男性受害者求助无门。‘逆光行动’提供了宝贵的田野资料。”
形势开始逆转。
然而,真正的风暴,出现在一个月后。
某国家级电视台决定播出《沉默的大多数》前两集试映版。节目组邀请了多方嘉宾进行现场讨论,包括妇联代表、法律专家、心理学家,以及一名匿名受访的男性家暴幸存者。
直播当晚,收视率飙升。
当纪录片播放到那位拳击冠军跪地求饶的画面时,全场寂静无声。
圆桌讨论环节,一位知名女权学者发言:“我支持关注男性受害现象,但我必须指出,将两者并列讨论,容易消解女性长期处于结构性弱势的地位。数据显示,女性遭受家暴的比例仍是男性的三倍以上。”
话音未落,那位匿名受访者举手请求发言。
他是位程序员,因长期被妻子辱骂、限制社交、经济控制而导致重度抑郁,曾两次尝试自杀。
“您说得对,数据上女性受害更多。”他平静地说,“但我想问一句:当我去心理科挂号时,医生问我‘你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当我报警时,警察劝我‘多哄哄老婆,别计较’;当我向朋友倾诉时,他们笑我‘堂堂男人这么脆弱’??这些反应,是因为我性别错了,还是因为整个社会都不愿承认男人也会受伤?”
他环视全场:“我不是来抢话语权的。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我的痛苦,必须比别人的轻才算合理?”
全场哗然。
十分钟后,#男性受害者现场反问女权学者#登上热搜榜首。
三天后,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发布声明:“家庭暴力是违法行为,任何形式的暴力都不应被容忍。我们将推动修订《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细则,明确将男性受害者纳入保护范围,并加强对基层执法人员的性别平等培训。”
这一刻,洪艺广在群里发了一句:“兄弟们,赢了。”
可陈默却没有笑。
他在剪辑室里反复回放一段从未公开的影像??那是他们在北方某小镇拍摄时偶遇的一幕: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农蹲在屋檐下喂鸡,脸上有道深深的刀疤。得知摄制组来意后,他沉默许久,才低声说:“俺老伴儿年轻时挺好的,后来得了癔症,总说我要杀她。半夜拿菜刀砍我,好几次差点没命。孩子们都说妈疯了,让我忍着。可忍了三十年,我现在连觉都不敢睡。”
摄像机没拍他流泪,但他浑浊的眼里,全是绝望。
这段素材最终被编入第九集《时间的伤口》。
影片上映前夕,陈默召集所有人开了最后一次筹备会。
“这部片子不会让我们更红,”他说,“反而可能让我们失去一些粉丝,得罪更多利益集团。但它值得做。因为我相信,真正的平等,不是把一种压迫换成另一种压迫,而是让每一种苦难都被看见,让每一个灵魂都有权利说:我疼,请帮帮我。”
发布会当天,六个人并肩走上红毯。
没有闪光灯追逐的喧嚣,没有品牌赞助的喧哗。只有数百名受助者及其家属自发前来,在场外拉起横幅:“谢谢你,让我们不再沉默。”
首映礼上,当最后一个名字出现在致谢名单时,全场起立鼓掌。
“特别感谢:一群比我更有勇气的女人。”
杨蜜靠在陈默肩上,轻声说:“你说过你要封镜,可我觉得,这才是你真正的开始。”
他握住她的手,望向银幕上那一张张曾躲在阴影里的脸,如今终于迎着光行走。
雨停了。
晨光穿透云层,洒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就像那些终于被听见的声音,微弱,却坚定地回响在这个时代最需要温柔以待的裂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