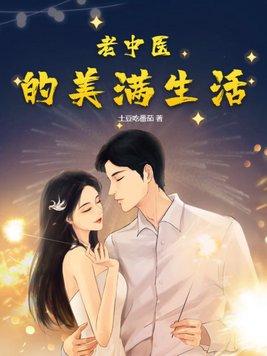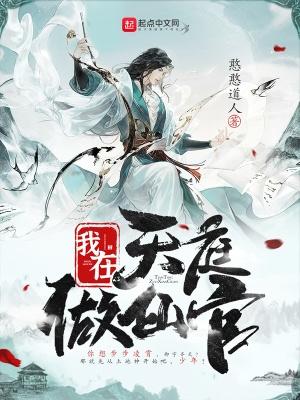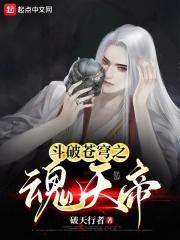BL小说>上玉阙 > 第七章 仙尊挥舞皮鞭抽的毕方轻哼爽爽爽(第2页)
第七章 仙尊挥舞皮鞭抽的毕方轻哼爽爽爽(第2页)
第二天,所有被“梦茧”感染的孩子都在同一时刻醒来。他们看着父母,忽然齐声问道:
>“你们小时候,也做过这样的梦吗?”
问题如钟鸣,荡开层层涟漪。家长们怔住,有些人猛然想起早已遗忘的童年梦境,泪流满面;有些人则惊恐地发现自己竟毫无印象,仿佛人生自懂事起才开始。
这场觉醒迅速蔓延。新一代巡灯使不再只是倾听者,他们开始引导梦境对话,建立“梦桥”网络??两人以上便可结盟,共享梦境通道,共同抵御外来精神入侵。更有大胆者提出:“既然敌人用梦来洗脑,我们何不用梦来启蒙?”
于是,“梦课”正式进入民间教育体系。孩子们每天睡前由导师引导进入特定情境:体验古人的苦难、感受异族的情感、甚至模拟百年后的世界。一位五岁男孩在梦中经历了真人殿焚书之夜,醒来后画了一幅画:一群大人举着火把烧书,而一个小女孩躲在墙角,手里紧紧攥着一页纸。他在画旁歪歪扭扭地写字:
>“我不怕火,
>我要把字藏进心里。”
此画被送往梦塾,挂在第十碑旁。哑童看了许久,最终拿起新炭笔,在墙上添了第三句铭文:
>“燃烧的书会重生,
>沉默的心才真正死去。”
岁月流转,又逢百年祭。
这一年的春分格外不同。当孩子们点燃记忆之火时,火焰不再是单纯的橙红,而是呈现出流动的文字色彩,仿佛每一簇火苗都在诉说一个故事。更令人震惊的是,第十碑遗址上的玉简突然升空,悬浮于断言岭上空,缓缓展开,显现出一段全新文字,似碑文,似遗嘱,似召唤:
>“你们已经学会了记住,
>现在,要学会遗忘。”
众人哗然。
长老会紧急集会,争论不休。难道又要回到“忘即安”的时代?难道觉醒的终点竟是重新封存真相?
唯有盲女弟子静坐不动。她伸手触碰空中玉简的投影,嘴角泛起一丝笑意:“你们误解了。不是叫我们忘记真相,而是提醒我们:并非所有记忆都值得背负终生。有些伤,需要时间愈合;有些恨,应当随风而去。真正的自由,不是被迫记住,也不是被迫遗忘,而是拥有选择的权利。”
她顿了顿,声音轻柔却清晰:
>“就像母亲不会永远责怪孩子的过错,
>历史也不该成为子孙的枷锁。
>记住该记住的,放下该放下的,
>才能让灵魂继续前行。”
这番话如春风化雪,悄然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忆园不再强调“必须铭记”,而是增设“释怀角”??人们可在此写下想要暂时封存的记忆,投入特制陶瓮,埋入地下三年。期满后自行决定是否开启。有人选择永远不挖,有人三年后再看,已能平静面对。
社会逐渐趋于平衡。觉醒者不再一味追责,施害者后代也不再一味逃避。一种新型伦理诞生:责任需承担,但宽恕亦可贵;真相应昭示,但慈悲不可弃。
多年后,那位手持笔的木偶被供奉于新建的“梦源祠”中央。每年春分,孩童们绕祠行走三圈,每人献上一个问题。这些问题不再被收藏或展示,而是在仪式最后投入净化之火,化为青烟升腾而去。
有人不解:“为何要烧掉孩子们的疑问?”
主持仪式的巡灯使微笑答道:
>“问题的价值,不在于被解答,
>而在于被提出。
>火烧去的是形式,留下的是勇气。”
而在极北雪原,少年守瞳人仍在雕刻。他的木偶已逾万尊,排列成环形阵列,环绕雪屋。最新一尊,面容模糊,性别不明,唯一清晰的是眼睛??睁得极大,像是正目睹某种不可思议之事。
有人问他:“你还等什么?”
他望着远方海平线,轻声道:
>“我在等下一个说‘我不信’的人。”
话音落下,海风忽起,卷起一片雪花,恰好落在木偶眼睑之上,瞬间融化,宛如一滴泪。
同一时刻,归书塔最深处,最后一块水晶棱镜彻底亮起。画面中,篝火依旧燃烧,孩子们的身影渐渐模糊,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浩瀚星空。其中一颗陌生的星辰缓缓亮起,不属于任何已知星座。
镜头缓缓推进,直至星核内部。那里,赫然浮现出一行微小却永恒的文字,仿佛宇宙本身在低语:
>“提问者永生,
>迷途者常在,
>持灯之人,永不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