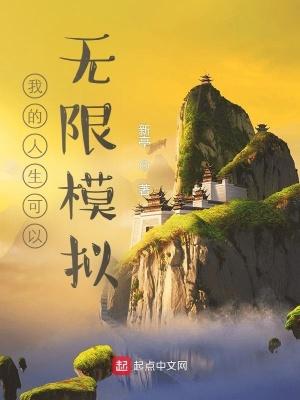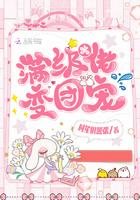BL小说>内娱顶流:从跑男出道 > 第三百九十一章 陪酒6k(第1页)
第三百九十一章 陪酒6k(第1页)
……
……
穿过曲径通幽的走廊,推开一扇厚重的、雕琢着复古花纹的实木门,映入眼帘的是一间极尽奢华却又透着古典韵味的包厢。
柔和的暖色灯光从精致的水晶吊灯上洒落,映照在光可鉴人的红木桌。。。
阳光斜照进空荡的教室,尘埃在光柱中缓缓浮动。张松文站在黑板前,指尖还沾着粉笔灰,那句“只要你还在说,光就不会灭”像一道刻痕,深嵌进时光里。他望着窗外??操场上的老槐树已抽出新芽,枝条轻摇,仿佛在回应某种无声的召唤。
手机震动起来,是静怡发来的消息:“巴黎那边来信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想把《播种者》纳入‘全球口述史保护项目’,建议我们启动第二季巡演主题:**迁徙与归途**。”
他没立刻回复,只是将手机轻轻放在讲台上,目光落在墙角那面旧旗上。“万物共生”四个字被岁月磨得有些褪色,却依旧挺立如初。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面旗帜,而是无数个名字、土地、眼泪和希望交织而成的信仰图腾。
两天后,剧社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排练厅里坐满了人,不只是原班成员,还有从全国各地自发赶来的年轻教师、基层文艺工作者,甚至几位退休的老知青。他们带着笔记本,眼神炽热,像是奔赴一场迟到多年的约定。
“不是我们要再去一次巴黎。”张松文站在中央,声音不高,却穿透了整个空间,“是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当世界开始倾听我们的故事时,我们该讲什么?”
顾顶翻开笔记本:“第一季讲的是‘出身’,讲我们如何从泥土中站起来;第二季,或许可以讲‘流动’??农民工进城、留守儿童守家、大学生返乡、灾民搬迁……这些人的脚印,本身就是一部活着的史诗。”
马小梅点头:“我在深圳直播时看到一个视频,有个姐姐在深圳做了二十年保洁员,每年只回家一次。她儿子不认识她,见面叫‘阿姨’。她说:‘我不是不想陪他,是我得活着,才能给他未来。’这话让我整晚睡不着。”
屋里一片沉默。老兵放下手中的鼓槌,低声说:“我当年参军走的时候,娘攥着我的手说:‘走得再远,别忘了回头看看路。’现在很多人走了,再也回不去了。不是不想回,是家乡变了,人也变了。”
“那就让戏替他们回去。”静怡忽然开口,眼睛亮得惊人,“我们可以设计一条‘虚拟归途’??舞台上用投影画出中国地图,每演一个人物,就点亮一座城市或村庄的名字。观众看到的不仅是故事,更是千万普通人用脚步丈量过的国土。”
王杰补充:“还可以加入真实录音。我去过甘肃一个空心村,全村只剩三位老人。他们对着录音机说话,像遗言一样:‘我是李桂花,七十八岁,住在大柳沟。要是以后没人记得这儿,至少还有这段声音。’听着心都碎了。”
会议持续到深夜。最终确定主题为《**行路者**》,分为五幕:离乡、漂泊、扎根、遗忘、归来。每一幕都将由真实人物原型改编,演出形式融合方言朗诵、即兴舞蹈、现场录音与互动影像。
决定一出,行动便如野火燎原。
马小梅带队前往珠三角,走访城中村、建筑工地、外卖站点,记录下三百多个打工者的故事。她在东莞一家制衣厂蹲点两周,跟一位女工同吃同住。那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晚上还要视频辅导女儿功课。她的梦想写在车间角落的便利贴上:“等攒够钱,开个小店,教孩子做手工。”
顾顶则北上东北老工业区,在废弃的厂区宿舍里采访下岗工人。一位老师傅拿出一本泛黄的相册,里面全是曾经的工厂合影。“那时候我们骄傲啊,全国一半的拖拉机是我们造的。”他说着说着哭了,“如今厂没了,人散了,连墓碑都不知道该往哪儿立。”
而静怡选择深入西部高原,追踪那些支教老师与留守儿童之间的羁绊。在一个海拔四千米的小学,她遇见了一个叫卓玛的女孩,每天徒步三小时上学,书包里除了课本,还装着给弟弟妹妹带的馒头。老师问她长大想做什么,她说:“我想当桥。这样弟弟妹妹就不用?河了。”
这些素材被一点点带回陇西,整理成剧本雏形。排练重新开始,节奏比以往更沉重,也更锋利。
有一次,一个饰演农民工的父亲演员,在念到“我给孩子寄了五年生日礼物,可他从没拆开过??因为他以为那是妈妈买的”时,突然失控痛哭。全场静默,没人打断,只有窗外风穿过瓦缝的声音,像一声声叹息。
张松文走上前,轻轻拍他的肩:“你不是在演别人,你是在替千千万万说不出话的人开口。哭吧,剧场本来就是让人流泪的地方。”
春去夏至,《行路者》进入合成阶段。舞台设计大胆突破传统:中央是一条长达二十米的“路”,由真实沥青、碎石、铁轨、水泥板拼接而成,象征中国城乡交错的现实肌理。演员行走其上,脚步声通过地埋传感器实时转化为背景音效??脚步越重,鼓点越沉。
最震撼的设计来自灯光。每当有人说出关键台词,头顶的LED矩阵便会投射出对应地点的卫星图像:北京回龙观、重庆筒子楼、乌鲁木齐大巴扎、杭州电商园区……地理坐标与情感坐标在此刻重合。
首演定在七月,地点不再是巴黎,而是北京国家大剧院。消息传出,票务系统瞬间崩溃,三万张票十分钟内售罄。主办方紧急增设十个城市同步直播点,并邀请百名一线劳动者免费观演。
演出当晚,暴雨如注。
但剧院外仍排起长队,许多人举着伞,手里攥着写着亲人名字的纸条。“这是我爸的名字,他在山西煤矿干了三十年。”“这是我姐,她在广州送外卖,三年没回家过年。”
大幕拉开,第一幕《离乡》以一段无声开场:十几个少年背着行李站成一排,身后是投影中的村庄剪影。母亲们默默塞进干粮,父亲们背过身去抽烟。没有音乐,只有火车鸣笛划破寂静。
紧接着,童声合唱响起:
>“背上包,走天涯,
>家门口的枣树还没开花。
>娘说等我回来吃月饼,
>可中秋过了十七个冬夏……”
台下已有啜泣声。
第二幕《漂泊》直接切入城市丛林。舞台分割成多个生活切片:地下室群租房里,五个男人挤在一张床上打牌;地铁末班车,白领女子靠在陌生人肩上睡着;凌晨四点的早餐摊,夫妻俩一边揉面一边争论要不要把孩子接到城里读书。
其中一幕引发全场震动:一位农民工父亲终于见到多年未见的儿子。两人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张桌子,沉默良久。父亲颤抖着掏出一张存折:“给你买房的首付,差六万。”儿子低头说:“爸,我不想要房,我就想小时候你能陪我看场电影。”父亲愣住,老泪纵横,全场灯光骤暗,只留一束光照在他佝偻的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