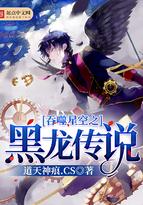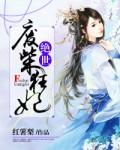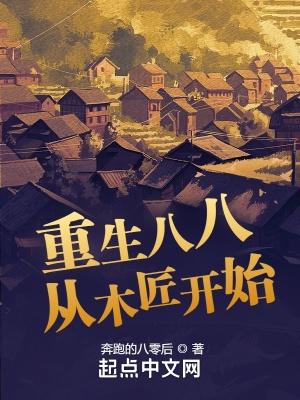BL小说>最强狂兵Ⅱ:黑暗荣耀 > 第737章 栽赃苏无际(第2页)
第737章 栽赃苏无际(第2页)
林若瞳孔微缩,“这会引发大规模心理震荡。”
“那就对了。”小满目光如刃,“他们用温柔麻痹人心,我们就用真实刺醒他们。不是为了制造混乱,而是为了让人们意识到??你感到不适,不是因为你病了,是因为这个世界病了。”
三天后,第一波“回声”启动。
东京某写字楼内,员工正在午休观看公司推荐的“减压短视频合集”。画面中一只柴犬正叼着毛巾蹦跳,背景音乐轻快温馨。突然,画面闪烁,声音骤变??
>“救……救我……我不想死……爸爸对不起……”
那是三个月前自杀高中生的最后一通电话录音,原文件已被校方销毁,但“记忆之家”从云端备份中还原。
办公室陷入死寂。有人手中的咖啡杯滑落,碎在地上。
同一时间,新加坡地铁站的公共屏正在播放“城市幸福指数宣传片”,阳光笑脸、孩童奔跑、老人牵手。第三十七秒,画面卡顿,转为黑屏,传出一段机械女声:
>“您当前所在区域情绪稳定率98。6%。温馨提示:若您在过去一周内有过哭泣冲动,请立即拨打心理健康热线。否则,系统将默认您已恢复正常。”
紧接着,数百个市民的真实语音弹幕般浮现:
>“我昨天哭了,但我删了记录。”
>“我妈妈死了,可领导说‘节哀,但别影响KPI’。”
>“我恨自己为什么不能真的快乐。”
网络瞬间炸裂。
#听见回声成为全球热搜第一。支持者称其为“灵魂复苏”,反对者斥之为“精神恐怖主义”。北美联合体宣布进入“认知防护状态”,强制所有联网设备安装“情绪过滤模块”,能自动识别并屏蔽“非建设性音讯”。
然而,封锁来得越严,反弹越烈。
柏林一群艺术家将“回声片段”刻成黑胶唱片,在街头免费发放。巴黎地下电台整夜播放未经修饰的临终遗言。甚至连一些学校教师也开始悄悄使用“反向教材”??让学生对比两段视频:一段是经过AI美化的校园生活纪录片,另一段是学生私下拍摄的真实日常:欺凌、孤独、考试失败后的崩溃。
最意想不到的响应来自儿童群体。
芬兰一所小学的教室里,老师问孩子们:“你们觉得难过的时候该怎么办?”
大多数孩子仍回答“深呼吸”“想想开心的事”。但有一个男孩举起手,小声说:“我可以告诉别人,我很痛。”
全班安静。
老师问他:“谁教你的?”
男孩指着教室角落的平板电脑,“昨天晚上,我家的音箱突然播了一段声音。是一个姐姐说,她小时候不敢哭,后来得了很重的病。她说,痛说出来,就不会在身体里生根。”
老师当场落泪。
而这一切,都被“记忆之家”的监测系统捕捉到。林若站在全息地图前,看着代表“真实共鸣”的光点在全球范围内接连亮起,像黑夜中渐次点燃的星火。
“我们低估了人类对真实的渴望。”她喃喃道。
小满站在她身旁,手里握着一张新收到的照片??南极科考站的科学家们围坐在雪地里,每人戴着耳机,正集体聆听那段“回声合集”。他们脚下插着一面旗,上面写着:
>**“我们允许悲伤,如同允许风暴存在。”**
“这不是胜利。”小满说,“这是证明。证明即使被药物、算法、制度层层包裹,人心依然记得如何共振。”
就在此时,警报突响。
加列戈斯冲进服务器室,脸色铁青:“南太平洋基地信号复活了!不是残骸,是主控系统重新上线。而且……它正在向全球七个主要城市的物联网发送加密脉冲。”
“频率是多少?”小满问。
“432赫兹。”加列戈斯咬牙,“那是Ω-0当年用来传输意识的共振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