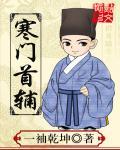BL小说>我的心动老板娘 > 第一千三百零五章 条件是必须的(第2页)
第一千三百零五章 条件是必须的(第2页)
>现在有了。
我的心猛地揪紧。
昭阳不知何时也撑伞跑了过来。她一句话没说,只是默默打开随身携带的应急灯包,取出便携式灯笼,轻轻挂在灯柱上。暖黄的光晕瞬间扩散开来,映照在女孩脸上,像一层薄薄的安慰。
接着,她从背包里拿出一个透明密封袋,里面装着一只纸折的渡船。她递给李婷,又递上一支防水笔。
女孩迟疑片刻,接过笔,在纸上写下几个字,折好塞进船中,然后小心翼翼放进灯笼底部预留的“信箱格”。
那一刻,风雨似乎都静了下来。
三天后,《夜航船》播出了这段录音。主持人声音低沉:“今夜的渡船,来自一位从未开口说话的女孩。她说:‘哥,我在南湖的灯下给你留了一盏灯。你说怕黑,可你看,现在连雨夜都有光了。你要不要回来看看?’”
节目播出当晚,那座灯点前摆满了蜡烛与鲜花。有人留下纸条:“我也曾想放弃。”“谢谢你替我说了那句话。”“明天,我想试试活下去。”
而李婷的母亲打来电话,哭着说女儿回家后第一次主动拥抱了她,还指着电视里的广播画面,用手语比划:“那是我的声音。”
昭阳听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翻出她珍藏的“心声印章”拓片,在背面添上新的一句:
**有些话,不必说出来才算存在。**
入秋之后,“城市微光计划”加速推进。一百个灯点陆续建成,覆盖老旧小区、城乡接合部、精神病康复中心、流浪者收容站……每个灯点都有独特设计:养老院旁的灯柱雕刻着盲文诗句;儿童医院外墙嵌入会变色的情绪感应灯;火车站地下通道则铺设了脚步触发式光带,行人走过,脚下便绽放一朵朵流动的花。
最令人动容的是位于殡仪馆外的那一处。起初居民反对强烈,认为“晦气”。但项目组坚持落地,并命名为“归途灯亭”。亭内设双声道录音系统:一侧录生者对逝者说的话,另一侧则播放过往留言精选。
有一位父亲连续七天前来录音。他儿子因抑郁症离世,年仅十九岁。他每次都说同一句话:“爸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要是你在,就好了。”直到第八天,他按下播放键,听见一个陌生少年的声音传来:“叔叔,我也想吃红烧肉。但我现在不怕黑了,这里有灯,还有很多人陪着我。”
他当场跪倒在地,痛哭失声。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另一位自杀未遂的高中生录下的回应。
昭阳听说这件事后,整整一天没说话。傍晚,她独自去了记忆之亭,赤脚踩在石板上,一遍遍按下手印。临走前,她在亭子角落埋下一个小陶罐,里面装着三百六十五张纸条??每张都是孩子们写给“另一个自己”的信。
“她说要等十年后再打开。”许雪晴告诉我,“她说那时候,也许有些人已经能亲口说出这些话了。”
十一月的一个清晨,市政府召开“微光计划”中期总结会。我带着昭阳出席,她穿着一件自制的小围裙,上面绣着“灯匠”二字,背后还缝了个迷你灯桥模型。
会议开始前,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站起来发言。他是本市著名社会学家,曾公开质疑该项目“形式大于实质”。
“我原本以为,这只是场温情表演。”他扶了扶眼镜,声音微颤,“可当我走进一家养老院,看见一位阿尔茨海默症老人颤抖着手指按下录音键,反复说着‘老婆子,我找不着家了’,而系统自动播放她二十年前录的情歌时……我才知道,这不只是灯,是记忆的锚点,是灵魂的回声。”
全场寂静。
昭阳忽然举手。主持人愣了一下,随即点头。
她走上台,没有讲稿,只是打开随身携带的录音笔,播放了一段音频??那是小宇的声音,经过半年语言训练,虽仍断续,却清晰可辨:
“我……想……告诉……所有……不敢说话的人……灯,不会……笑话你。它只会……等你。”
话音落下,掌声如潮。
散会后,老教授特意找到昭阳,蹲下身,认真地说:“小朋友,我能申请成为你们的‘老年灯语志愿者’吗?我想帮更多老人找回遗失的声音。”
昭阳用力点头:“欢迎加入灯匠团。”
冬天来临,第一场雪悄然落下。城市披上银装,路灯在雪幕中晕出一圈圈柔和的光晕。昭阳提议举办“冬夜灯语节”,邀请所有参与过灯点建设的人齐聚南湖榕树下,共同点亮一面“千声墙”??由一千个小型扬声器组成的艺术装置,每个喇叭播放一条真实录音片段。
那天夜里,雪花纷飞。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手持纸灯,静静伫立。当千声墙同时启动,无数声音交织响起:
“妈妈,我想你了。”
“对不起,当年我没勇气娶你。”
“谢谢那个捡起我药瓶并报警的陌生人。”
“我终于敢说出来了:我是个同性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