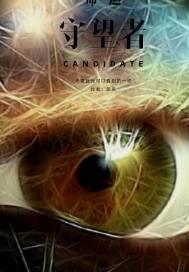BL小说>伊塔纪元 > 第一百七十七章 阵眼(第2页)
第一百七十七章 阵眼(第2页)
良久,招娣从后排站起来。她拄着一根藤杖,脸上皱纹如地图般深刻。“我记得苏莺最后一次公开演出。”她说,“那天她唱了一首没人听过的歌,调子跑得离谱,歌词也不押韵。台下很多人离场,说这是亵渎艺术。可我留下来了。因为我听出来了??那不是歌唱,是她在挣脱。”
她看向大尼:“你说我们在压抑真实?也许吧。但我们也在学习分辨。不是所有情绪都值得释放,不是所有记忆都应该复活。关键是,谁来决定?凭什么决定?”
“所以才要有‘识镜会’。”角落里传来阿禾的声音。她不知何时也来了,手里抱着那台老旧录音机。“我们不教答案,只教提问。就像小禾给孩子的书签。我们要让每个人都知道??你可以不信,可以怀疑,可以沉默,也可以改写。”
这时,那个小女孩举起了手。她是今天第一个走进“疑言堂”的孩子。
“我有个问题。”她说,“如果连‘真实’都可以被改写,那还有什么是我们能抓住的?”
全场目光落在她身上。
大尼蹲下来,与她齐高:“有的。比如你现在提这个问题的样子,就是真实的。你心里真的在困惑,而不是背诵别人教的答案。这种‘不确定’,恰恰是最难伪造的东西。”
“那……”她犹豫了一下,“我可以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吗?就是还没写完的那种?”
“当然。”大尼微笑,“而且我们不会催你结尾。”
于是小女孩站上临时搭起的小台子,声音不大,却清晰可闻:
“从前有个女孩,她发现所有的书都被锁在图书馆最深处,钥匙由校长保管。他说这些书太危险,会让人做噩梦。可女孩偷偷打开了一本,里面全是空白页。但她继续翻,突然看见自己的脸出现在纸上,正张嘴说话。她吓坏了,合上书就跑。可第二天,她发现自己说的话越来越少,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嘴里被抽走了……”
她停下来,喘口气:“我现在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她会找到其他孩子一起砸开书库?或者学会用画画代替说话?又或者……她根本逃不出去?”
没人催促,没人评判。
只有阿禾轻轻按下录音键,磁带开始转动,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雨落屋檐。
散场后,大尼独自走到海边。月光洒在沙滩上,映出长长的影子。他蹲下身,用手指在湿沙上写下一句话,又慢慢抹去。写下,再抹去。反复多次,直到潮水涌上来,带走最后一道痕迹。
他知道,有些话不必留存于纸面。它们活在语气的停顿里,活在听众皱眉的瞬间,活在某个孩子半夜惊醒后喃喃自语的疑问中。
回到居所,他翻开一本新日记本??不是为了记录过去,而是为了练习尚未到来的言语。第一页只写了三个字:
“试试看。”
第二页是一段对话草稿,模拟两个立场完全相反的人辩论“是否该销毁所有伊塔遗留技术”:
>A:那些系统害了多少人?它们设计眼泪、安排悲喜,连死亡都要按剧本走!留着就是隐患!
>B:可如果没有它们,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笑?就像盲人学画,总得先临摹光影。
>A:可临摹久了,会忘记自己原本想画什么。
>B:所以更要保留,作为镜子,提醒我们曾迷失过。
>(中间空白)
>??或许真正的危险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我们一旦摆脱控制,就开始渴望另一种秩序。
他停下笔,望着窗外。夜空中星辰密布,其中一颗格外明亮??那是北极圈那位老人日复一日发送摩斯电码的方向。虽然信号从未抵达任何接收站,但启言镇的孩子们已把它编成了童谣:
>点划点划,我们醒着呀,
>虽然没人听见,也要说话。
第二天清晨,邮局旧址传来喧闹声。原来是来自滨海工业区的代表到了,带来一台被改造过的“情感调节仪”??曾经用来检测居民情绪波动、自动投放镇静剂的机器。如今外壳被涂成七彩,喇叭口插满了野花,内部电路重新焊接,变成了一台“随机故事发生器”。
只要投入一枚硬币,它就会吐出一张纸条,上面印着由算法拼接而成的荒诞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