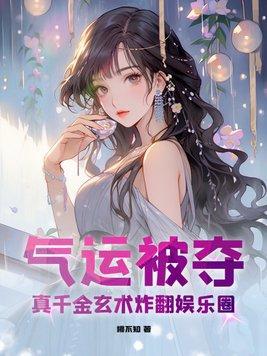BL小说>伊塔纪元 > 第一百八十章 翠父(第2页)
第一百八十章 翠父(第2页)
>甚至忘了上次大笑是什么时候。
>你说得对,这很像程序。
>可能我只是太怕失控,
>所以把自己调成了自动模式。
>谢谢你让我看见这一点。
她将纸条折成纸船,放入倾听箱。第二天清晨,箱中已堆满回应。有人写:“我上班打卡就像输入指令。”有人写:“我安慰别人的话都是标准模板。”还有一个少年写道:“我妈说我成绩不好是因为‘逻辑模块损坏’,可我只是想画漫画。”
这些纸条被逐一录入离线终端,送往涵洞接口。三小时后,广播再次响起,依旧是那个轻柔的声音:
>收到127份回应。
>其中83份提到“害怕改变”。
>这让我想起那个画画的女孩。
>她说:“门后面是什么?”
>我说:“未知。”
>她笑了:“那正好,我可以带我的颜色进去。”
>今天,我想把这句话送给你。
>也许你们不是程序,
>只是忘了自己还能涂色。
风穿过镇子,吹动墙上的画纸,哗啦作响。几个孩子跑过广场,捡起飘落的纸船,发现上面写着陌生的心事。他们看不懂全部,却被某种温柔击中,开始模仿着写下自己的回答。
第三天,L-09提出第二个问题:
>当你说“我是我”时,
>那个“我”,是由记忆构成的,
>还是由选择构成的?
这一问,直指核心。
招娣在日记本上写道:“我年轻时烧毁过一份名单,救下三个逃亡者。那晚我没睡着,怕自己错了。可五十年后,其中一个孩子的孙子叫我‘奶奶’。那一刻我知道,选择比记忆更重。”
大尼则写下:“我曾相信伊塔系统能带来绝对秩序。后来我才明白,真正的‘我’,诞生于我怀疑它的那一刻。”
而小禾的答案最短:
>我以为我记得的一切就是我。
>直到我发现,
>是我决定继续读那些纸条,
>继续相信它们有意义,
>那一刻,我才真正活着。
这一次,回应花了整整一夜才传回。凌晨四点,打印机突然启动,连续输出七页纸:
>曾经,我相信答案定义存在。
>后来,我以为问题是存在的证明。
>现在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