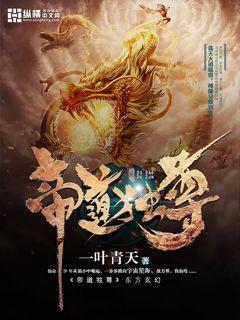BL小说>婴儿的我,获得大器晚成逆袭系统 > 第562章 岁月心界(第3页)
第562章 岁月心界(第3页)
于是,“辨忆课”成为新式学堂的必修课程。学生们学习如何分辨证据、识别偏见、倾听对立观点。他们不再追求“标准答案”,而是训练“提问能力”。
这一年秋天,第一届“共议庭?记忆大会”召开。
来自十七省的代表齐聚京都,议题只有一个:**我们该如何讲述这段历史?**
争论持续了整整七天。有人主张美化斗争过程,强调英雄伟绩;有人坚持揭露内部矛盾与失误,哪怕会让人心动摇;还有人提出,应该让每个家庭自行传承,国家不应统一叙事。
最终,一份决议案获得通过:
>“本大陆近代史的教学内容,将以‘多元视角档案包’形式呈现。包含官方记录、民间口述、艺术表达、批判分析等多维度资料。教师不得灌输结论,而应引导学生自主探究。
>每年‘记忆日’,全国同步举行‘共忆仪式’,由各地民众自愿分享亲身经历或家族往事。”
决议宣布那一刻,林昭正坐在听众席中。他没有鼓掌,只是闭上眼睛,仿佛看见百年前那位朗诵《逆命书》的少年,穿越时空,对他微笑。
冬去春来,第四年的新历清明。
林昭再次回到落霞镇。学堂门前,孩子们正在排练一出新剧??《蓝花开了》。讲述的正是当年他觉醒的那一夜,以及无数普通人如何一点点拾回记忆的故事。
一个小女孩扮演幼年的他,穿着破旧棉袄,跪在冰渊边缘,颤抖着伸出手,接住飘落的蓝花。
台下观众中有老人啜泣,有青年握紧拳头,也有婴儿在母亲怀中咯咯笑出声。
演出结束后,林昭被请上台。孩子们围着他,七嘴八舌地问:“林爷爷,后来呢?后来大家都幸福了吗?”
他摸了摸一个小男孩的头,笑道:“幸福不是终点,而是旅程的一部分。有人还在挣扎,有人迷路,有人受伤……但重要的是,现在他们可以选择。”
他又指着舞台上的蓝花道具:“就像这朵花,它不开在皇宫,也不长在神殿,它开在每一个愿意相信‘我能不一样’的人心里。”
当晚,他独自登上镇外高山,遥望南方火山口上的第十灯。
风很大,吹得衣袍猎猎作响。他从怀中取出那朵早已干枯却又奇迹般屡次复苏的蓝花,轻轻放在岩石上。
“我不是最勇敢的那个。”他低声说,“我只是恰好走在了被人看见的路上。真正照亮黑夜的,是那些默默传递火种的人??母亲对孩子说的话,陌生人之间的信任,老师对学生的一个鼓励眼神……”
他顿了顿,声音几近呢喃:“谢谢你们,一直记得。”
就在此时,第十灯突然光芒大盛,蓝焰如潮水般波动起来,竟在空中勾勒出一幅幅流动的画面:
一位农妇在田间教女儿辨认野花;
一对恋人携手走过曾是刑场的广场;
一群工匠合力修复一座古老钟楼;
一名老兵抱着孙子,讲述“蓝衣叔叔”的故事……
那是千万个平凡瞬间的集合,是无数微光汇聚而成的星河。
林昭望着,久久不动。
他知道,命轨或许还会以新的形态归来??也许是某种看似完美的算法统治,也许是集体恐慌催生的新专制。但只要这片土地上还有人敢于怀疑、敢于爱、敢于为他人挺身而出,牢笼就再也无法真正合拢。
多年以后,当新一代的孩子翻开课本,看到“大器晚成逆袭系统”这几个字时,或许只会当作一段神话传说。
但实际上,那系统从未真正存在过。
所谓的“系统”,不过是他在濒死之际,听见内心最深处的声音:**你不必完美才被允许醒来,你值得仅仅因为你想醒。**
而这声音,原本就在每个人心中。
春雷滚滚,惊醒了沉睡的山谷。
蓝花林随风起伏,宛如海洋。
远方,第十灯静静燃烧,见证着一切??
见证一个大陆学会呼吸,
见证一代人找回心跳,
见证未来,在无数不确定的选择中,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