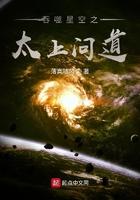BL小说>盐祸猪六戒 > 2030(第18页)
2030(第18页)
沈亭山笑着点点头,道:“我和一同去。”
陈脊与沈亭山整好队伍正准备一同去往坟场,身后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孙文鹏远远便高声喊着:“堂尊,请留步!”
他双手将公文递上,气喘吁吁道:“绍兴知府洪州今日就到山阴,堂尊应当亲自去迎接才是。”
陈脊一听顿觉头疼。
“这些事素来是你操办,这回仍是你去便是了。”陈脊推脱道。
孙文鹏压低声音道:“知府大人这时候来,只怕是为了近日盐祸一事,下官……恐不好处理。”
“上官问什么照答便是,纵有何不满,也只能是我的过错,与你不相干。”
有这话,孙文鹏便心安了。
亲民、教民、断案不过是表面文章,陈脊乐意做便让他做去。孙文鹏明白,接待上官、收支钱谷才是加官进爵的关键。陈脊愿意将这些事放给他做,他求之不得。
然而他面上仍佯装为难,叹道:“堂尊,话虽如此说,但来者毕竟是”
“行了。”陈脊打断道,“你照办便是了。”
沈亭山暗自思忖一阵,又回头瞧见尹涛气定神闲的模样,若有所悟,点了点头,对陈脊道:“开棺要紧。”
从横山河的金山码头右侧绕过,沿小路进山,不多时便来到一大片林场。荒草冷木深处立着一块块墓碑,有的新刻,有的斑驳,乃是一大片墓地。
陈脊并非山阴人士,父亲本因回乡安葬。然老父深知山阴事务繁杂,遂留下遗言,就近安葬便可,未免陈脊挂怀,还解释是为了死后能看着陈脊将这一方土地治理得井井有条。
陈脊穿过林木,一直走到最里边的墓穴才停下,“先考陈言路之墓”几个字分外扎眼。
陈脊道:“容我先祭拜过先父,再行开棺。”
沈亭山点头,借这时间,他绕着坟墓走动,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线索。他往南多行几步,注意到在众多墓碑之外还有几个微微隆起的小土坡。他之前来的时候是深夜,所以没有注意到这些。他回头走去,差役正好领着一众百姓而来,回禀道:“按照沈翰林的意思,百姓召集到了。”
沈亭山颔首,然后问道:“那几处小土坡怎么回事?”
差役垫脚看了几眼,回道:“是无主孤魂,随手埋了。”
沈亭山听后不置可否,领着众人回到墓前,这时陈脊已祭奠完毕,眼眶殷红。
百姓都觉得奇怪,为何要召集自己来这墓地,私底下悄声议论了起来。
沈亭山举目望去,扫视周遭众人,将各色人等都细细打量了一方,然后沉声道:“诸位皆知,近来山阴灾祸频频。陈知县为查明案情真相,几乎是夜不能寐。幸而圣上庇佑,如今案件有了新的线索,这墓穴便是破案的关键所在。为天地正气,还枉死者以清白,让山阴恢复安宁,陈知县不惜挖掘生父之墓来查案。今日特请诸位前来做个见证。”
此言一出,众人皆惊。
掘生父之墓,这陈知县是不要命了?
一时间,百姓之中,议论什么的都有,这可是比亲手弑父还要丧良的行径。
沈亭山早已预料到百姓会是如此反应,可他还是不得不这样做。为官之难,非在于政务,而在于世情人心的多变。身为父母官,若能得上官的援助,又能得士绅百姓的拥戴,同时能与同僚和衷共济,便是最佳之境。若三者只得其二,还尚有可为。
然而,若是如陈脊这般,本就三者全无,还要再做天理不容之事便是难了。
好在三者之中,百姓最易左右。如今,他只能尽力帮陈脊争取百姓支持,否则只怕陈脊要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沈亭山高声道:“陈知县深知此事的危害,然而百姓的安危更为重要。凶手在山阴害人无算,手段残忍至极。诸位想想,这段时间有多少人无辜被毒杀,却误以为是疫病所致。若不除去真凶,山阴难得太平。陈知县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个人荣辱,但求诸位的支持与谅解!”
百姓们明白过来了,开始有人喊叫:“支持陈知县!”
“支持陈知县!”
“开棺!查明真相!”
许多声音响了起来。
陈脊望着群情激奋的百姓,心里竟涌上酸楚。这样的场面,他曾多次在梦过,众人拥护,民心所向。可当一切真的变为现实,他却像堵了石头般难受。
他没有再看百姓,而是望向差役,一声令下,众人便开始动手了。
陈脊紧盯着坟墓,沈亭山则再次打量起围观人群,这里有百人之多,其中有几个正是沈亭山特地交代要带来的人。糖水贩欢哥及卖糕饼的刘大立在人群中,静静看着。尹涛持剑立在人群两边,神色淡然。马荣躲在人群的后头,是最方便离开的位置。
棺木埋得不深,很快便在土中初现。坟场临近横山河,土质松软湿润,昨日又下大雨,地下水位较高,棺木几乎浸泡在泥水中。几个差役一声惊叹,拿着锄头、铲子不知所措。
“慢着!”就在这时,远处忽有叫声传来。
陈脊循声回头,见孙文鹏领着差役拥着一人,沿小路进入树林,来到坟前。
孙文鹏不是去接待贵客?那这所拥之人应就是绍兴知府洪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