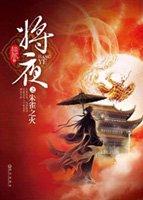BL小说>炮灰的人生2(快穿) > 2458杀猪娘子 二十五(第1页)
2458杀猪娘子 二十五(第1页)
山道上的薄雾还未散尽,林知意站在记忆学堂的院门口,望着远处蜿蜒入云的小径。风从西北吹来,带着黄沙与草籽的气息,也带来了新的消息??南疆三十六寨联名请愿,请求派遣“讲史人”前往传授《种火者》。信是用一种混合了古苗文与官话的杂体字写成,笔迹稚嫩却坚定,末尾按着七枚不同颜色的指印,像是燃烧的火焰。
她将信纸轻轻压在案上,目光落在墙角那支铁笔铜戒上。十年了,它依旧冰冷如初,却不再只是苏禾留给她的遗物,而成了千万人手中传递的符号。阿满如今已十七岁,身形挺拔,眼神清明,正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在校场边练习刻字。他们用烧硬的竹片在陶板上一笔一划地写下:“谁该为饥饿负责?”“凭什么?”“我们识字。”
林知意走过去,蹲下身,问最小的那个孩子:“你知道这句话是谁最先问的吗?”
小女孩摇头,又点头:“是……是我奶奶说的。她说,五十年前,有个男人拿着账本去县衙,就问了这一句,然后就被押走了。”
林知意轻抚她的头:“他叫陈大川,是你曾祖父的堂兄。他没走掉,但他问的那一句,活到了今天。”
孩子睁大眼睛:“那我也能问吗?”
“当然能。”林知意微笑,“而且你要大声问,问到所有人都听见。”
午后的阳光斜照进学堂,空气中浮动着尘埃般的字粒。这些年来,她不再只是送书的人,而是教人如何把书种进土里,让它生根发芽。每一所新成立的记忆分堂,都必须完成三件事:第一,抄录并传送出至少一部禁史;第二,建立本地“无名册”,记录那些被官方忽略的死亡、失踪与抗争;第三,选出一名“首问者”??通常是村里最敢提问的孩子,佩戴铁笔徽章,象征火种的继承。
就在昨日,南方传来消息:云溪镇的“首问者”是个十二岁的盲童,靠听声记下了整部《税吏之影》,并在祠堂前当众背诵。官府派人抓捕时,全镇百姓自发围拢在他身边,一人接一句,将全文完整复述了一遍。士兵们最终退去,因为法律无法惩罚“所有人”。
林知意知道,这场火已经脱离了她的掌控,也不再需要她亲自点燃。但她仍不能停下。因为还有太多地方,连“为什么”这三个字都被嚼碎咽下。
当晚,她在灯下展开一张新绘的地图。这一次,她用红墨标出了尚未点亮的区域??北境雪原、东海孤岛、西南密林深处的百越部落。她在每个空白点旁写下一句话:
>“此处无人讲史。”
>“此处尚不知自己有记忆。”
>“此处的孩子,还未学会提问。”
她正欲落笔标注下一个路线,忽听门外脚步急促。阿满推门而入,肩头沾满夜露,怀里紧抱着一只破旧的皮囊。
“师父,”他喘息未定,“我在北坡的石缝里发现了这个。是用三层油布裹着的,外面还缠着铁丝……上面有您的名字。”
林知意接过皮囊,手指触到那熟悉的纹路时,心猛然一沉。这是《九州问录》特制的封存方式,只有巡行者之间才懂。她小心翼翼拆开,取出一卷残破的竹简,上面赫然写着四个朱砂大字:
**《帝王之罪》**
她呼吸一滞。这不是她曾携带的章节,也不是苏禾手稿中的内容。这是一部全新的、从未面世的篇章,记载的是当今圣上登基前,在边军任监军时下令屠戮三百降俘之事。那些人本已放下武器,只求归乡务农,却被以“隐患难除”为由,尽数坑杀于山谷之中。事后朝廷宣称“叛贼伏诛”,并将此役列为“永昌大捷”。
更令她震惊的是,竹简末页附有一份名单??共四十七人,全是当年参与屠杀的士兵或文书,如今大多已在朝中担任要职。其中一人,竟是当朝兵部尚书。
“这东西……从哪来的?”她低声问。
阿满摇头:“发现它的山洞口插着一根带节的竹枝,旁边还有双倒穿的布鞋。是‘传火暗号’,说明它是被人特意藏在这里的。”
林知意立刻明白:有人在传递信息,而且是来自权力核心内部的背叛者。或许是某个良心未泯的老臣,或许是某位知晓真相的宫人,甚至……可能是太子本人。
她不敢久留此物于学堂,当夜便召集几位可信的弟子,将竹简内容逐字誊抄成三份,分别封入陶罐,埋入不同方向的山腹之中。原件则被她投入灶膛,化作灰烬。但她留下了那份名单的副本,藏于《疑思启蒙》的夹层内。
三天后,朝廷使者再度降临。
这次来的不是监察官,而是礼部侍郎亲率仪仗,宣称奉旨宣读嘉奖令:因林知意“兴教化民,启智育人”,特赐“贞慧先生”封号,并邀其赴京主持新设的“民间修史局”。
村中众人皆惊。有人欢喜,认为这是朝廷认可的标志;也有人警惕,觉得这是收编与驯化的开始。
唯有林知意冷笑。
她太清楚这种招安的本质??让你进入体制,赋予你虚名,再一点点磨去你的锋芒。所谓的“修史局”,不过是将真实的历史重新筛选、修饰,变成另一种谎言的容器。
但她没有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