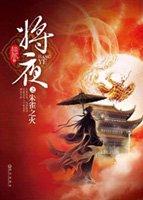BL小说>炮灰的人生2(快穿) > 2458杀猪娘子 二十五(第2页)
2458杀猪娘子 二十五(第2页)
“我去。”她说,“但我要带十名学生同行。”
侍郎皱眉:“女子不得入阁观典,何况孩童?”
林知意直视他:“若不准学生随行,那我宁可终身执教荒野。请问大人,您是要一个听话的修史官,还是一个真正的‘记录者’?”
对方语塞,只得应允。
临行前夜,她在学堂后山召集所有“传火小组”成员,举行了一场秘密仪式。每人领取一枚新制的铁笔徽章,背面刻着一行小字:“火可熄,问不亡。”她将地图交予阿满,叮嘱道:
“我不在时,你便是这里的‘守灯人’。每月十五,按既定路线发送一次信号。若有异动,立即启用‘断链计划’??销毁所有明文记录,转为口传心授。”
阿满郑重跪拜:“师父放心,火在我手,亦在民心。”
车队启程那日,全村人再次列道相送。孩子们齐声朗诵《种火者》开篇词:
>“火非天降,乃人所燃。
>一问如星,可照百年。
>不惧黑幕重重,只怕万马齐喑。
>故吾辈执笔,非为留名,只为不让沉默成为习惯。”
林知意坐在车中,眼含热泪,却笑得坦然。
京城比她想象中更加辉煌,也更加压抑。朱雀大街宽阔如河,两旁楼宇巍峨,琉璃瓦在阳光下泛着冷光。可在这繁华之下,她看到的是无数低头疾行的百姓,听到的是街角巷尾刻意压低的对话。这里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恐惧??不是对暴力的畏惧,而是对言语的自我审查。
修史局位于皇城西侧一座独立院落,名义上隶属翰林院,实则受内廷直接监管。局长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学士,表面温和,言语间却处处设限。他递给林知意一份拟好的编纂纲目,其中关于“永宁六年民乱”的条目,仅允许写作:“地方偶有骚动,经官府妥善处置,现已安定。”
林知意当即将笔掷于案上。
“若只能写这些,那我不如回西北种田。”
老学士叹气:“姑娘,你以为我们不知真相?可有些事,揭得太快,反会引火烧村。不如徐徐图之,以柔克刚。”
林知意凝视着他:“您年轻时,是否也曾想做个说实话的人?”
老人浑身一震,良久无言。
当晚,她并未入睡。她取出藏在鞋底的微型炭笔,在寝房墙壁上悄悄拓下皇宫布局图的一部分。这是她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每到一处,必记地形、人流、守卫轮换时间。她还在袖中藏了一小包药粉,遇水即显字,可用于密写。
几天后,她借整理档案之机,终于接触到皇家秘档库的外围。那里收藏着历代奏折、战报与地方呈文的原始副本,虽经删改,但仍残留大量未被抹净的痕迹。她发现,许多“已平”“无事”的报告背后,都有墨迹涂抹的数字与姓名,仿佛历史正在纸上挣扎呼救。
她开始悄悄抄录。
白天,她在修史局装作顺从,撰写一些无关痛痒的“民俗考”;夜晚,则潜入偏殿,利用月光与特制药水还原被涂改的文字。她将所得情报分成若干碎片,通过进城采买的弟子们,以童谣、谜语、绣花样等形式,悄然散播至市井。
一个月后,京城街头突然流传起一首儿歌:
>“灯笼红,灯笼亮,
>官说太平百姓丧。
>雪夜三百锄头响,
>问完‘凭什么’,再无返乡。”
起初无人在意,可当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巷口哼唱时,巡逻的禁军开始紧张。有人举报传唱者,却发现家家户户都在教这首曲子??母亲们说:“好听,孩子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