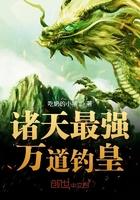BL小说>让你下山娶妻,不是让你震惊世界! > 第1561章 果然还是自家兄弟好(第3页)
第1561章 果然还是自家兄弟好(第3页)
留言区却炸了锅:
>“这是我第一次觉得,孤独也可以被陪伴。”
>“听着听着,我哭了。原来我不是麻木,只是太久没人听我说话。”
>“我想给我爸打个电话,告诉他,那次打架,是我先动手的。”
菲律宾的声波浮标项目扩展到了太平洋岛国。渔民们发现,不仅珊瑚再生加快,连鲸鱼也开始改变迁徙路线,常常围绕浮标区域盘旋游动。海洋学家推测,这些哺乳动物能感知到人类情感振动的频率,并将其视为某种“群体呼唤”。
一位老渔夫在接受采访时说:“从前我们祈祷神明保佑平安。现在我们对着浮标说话。奇怪的是,大海真的回应了。”
时间进入第三年。
某日,联合国秘书长亲自来到雪山木屋,身后跟着一支纪录片摄制组。他没有要求采访,也没有提出合作,只是在门前站了十分钟,然后掏出一封信,贴在墙上:
>“我曾否决三项关于‘情绪权利’的提案,理由是‘时机未成熟’。昨天,我八岁的女儿问我:‘爸爸,为什么大人们总说没事,明明他们都在哭?’我答不上来。今天,我来补交我的第一份作业。”
星芽带着孩子们来了。她们在山坡上搭起一座露天剧场,上演一部名为《静音之前》的话剧,讲述一个家庭三代人如何学会说“不”的故事。最后一幕,祖母终于对已故丈夫的画像说出压抑五十年的话:
>“我不是不想离婚,我是怕被人说闲话。
>可我现在知道了,沉默不是美德,是共谋。”
全场观众起立鼓掌,许多人相拥而泣。
明川和阿萝坐在人群最后,彼此依偎。
“你觉得,这一切会持续下去吗?”阿萝问。
“不会。”明川说,“总会有人重新发明谎言,总会有人用‘为你好’来封口,总会有人把痛苦包装成坚强。
但也会有新的孩子举起手,问出那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必须开心?’
只要这个问题还在,声音就不会断。”
当晚,他又一次爬上山顶,取出母亲的老麦克风,哼起《归心引》。
这一次,回应他的不仅是山谷的共振。
遥远的冰岛、非洲、南美、北极观测站……数十个声种站点同时接收到同一段波频。伊琳娜在日志中写道:
>【全球声波网络首次实现自发同步。
>不是由技术驱动,而是由情感牵引。
>我们检测到一种新型共振模式,暂命名为‘人类共频’。
>它无法被武器化,也无法被屏蔽。
>唯一触发条件:真实。】
明川放下麦克风,仰望星空。
他知道,这个世界依然充满谎言,仍有千万人不敢开口,仍有权力试图驯化声音。但他也看见,地铁里有人摘下耳机,转头对陌生人说:“你看起来很难过,要聊聊吗?”;教室里有老师蹲下身,对孩子说:“哭出来没关系,我在这儿”;病房中,子女终于对弥留的父亲说:“爸,我原谅你了,你也该原谅自己。”
这些声音微弱,却坚韧。
就像那盏永不熄灭的蓝灯,在风雪中静静燃烧,告诉每一个迷途的人:
你不必完美才能被听见。
你只需要真实。
你只需要开口。
风起了。
灯,依然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