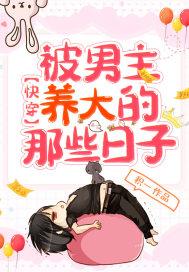BL小说>重生七零:开局打猎养家,我把妻女宠上天 > 735天大的好消息(第1页)
735天大的好消息(第1页)
电报按字收费,言简意赅,但字里行间却透着一股掩饰不住的喜悦和期盼:
“高考已毕,我与明亮自觉尚可,一切顺利,九月应可赴京。父字。”
宋婉清拿着那张薄薄的电报纸,反复看了好几遍如释重负而又无比欣喜的笑容。
她将电报递给刚从单位回来、额头上还带着汗珠的赵振国。
“振国,你看!爸发来的电报!他和明亮……考得应该不错!爸说,九月初就能来北京了!”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激动地颤抖。
赵振国接过电报,仔细读着那寥寥。。。。。。
秋收过后,稻谷归仓,青山村的夜晚变得格外宁静。赵振国却依旧没有停下脚步。清晨五点,天还未亮透,他已穿好外套,轻手轻脚地走出卧室,生怕惊醒还在熟睡的小丫和王秀兰。厨房里,灶台上温着一壶小米粥,是他昨夜睡前特意留下的火。他掀开锅盖,热气扑面而来,像极了南岭山间初升的雾。
他端着粥坐在院中石凳上,一边吃一边翻看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那本子已经泛黄卷边,密密麻麻记满了数据、草图与会议要点,甚至夹着几片干枯的稻叶和竹屑。这是他重生以来的日志,从七零年那个饥寒交迫的冬天开始,一笔一划写到了今天这个灯火可亲的时代。
手机震动起来,是林晓发来的消息:“赵老师,少年科学院刚收到教育部回函,国家科技馆想把咱们的‘智能农田模型’做成常设展区,永久陈列。”
赵振国盯着屏幕看了许久,轻轻回了一句:“告诉孩子们,让他们自己决定展陈方案??这是他们的成果。”
他放下手机,抬头望向东方。晨光正缓缓爬上山脊,将整座南岭染成金红。远处的光伏板阵列在朝霞中熠熠生辉,如同大地睁开的眼睛。他知道,这双眼睛不只是为了照亮村庄,更是为了唤醒更多沉睡的土地。
上午九点,村委会会议室再次坐满了人。不只是村两委成员,还有青年技术组、妇女创业队、非遗传承班的代表,甚至连程大山也由儿子推着轮椅来了。他的气色比前些日子好了许多,虽然说话仍有些吃力,但眼神清亮如昔。
“今天召集大家,不是汇报成绩,而是谈风险。”赵振国站在投影幕前,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我们走得太快,有些人已经坐不住了。”
话音刚落,林晓便接道:“昨天省里有个调研组私下找我谈话,暗示咱们的‘分布式决策系统’涉嫌‘架空基层组织权力’,建议暂缓推广。”
“不止如此。”程志远补充,“县信用社那边突然收紧了对妇女合作社的贷款审批,理由是‘风控升级’。”
一名返乡大学生举手:“我在政务平台提交的创新项目申报,被三次退回,每次都说材料不全,可我明明按清单准备了全部文件。”
会议室一时沉寂。窗外风吹过稻田,沙沙作响,仿佛天地也在低语。
赵振国缓缓起身,走到窗前推开木格窗。“你们知道我最怕什么吗?”他背对着众人,“不是失败,不是质疑,而是当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信任机制时,有人用制度的名义把它一点点磨碎。”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每一张脸:“所以,我宣布??从即日起,‘青山模式’所有核心系统源代码、运营逻辑、财务审计流程,全部开源公示,接受全社会监督。”
“什么?!”有人失声叫出。
“你疯了吗?”林晓猛地站起,“一旦公开,竞争对手可以照搬,别有用心的人更可能恶意攻击!”
“正因为会被人攻击,才更要坦荡。”赵振国声音不高,却字字如锤,“我们不做暗箱操作,也不搞特殊待遇。如果这套体系经不起阳光暴晒,那它就不配被称为‘未来乡村的样板’。”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我已经联系了几家权威媒体和第三方技术机构,邀请他们入驻村庄三个月,全程记录、评估我们的运行机制。欢迎质疑,欢迎挑刺,但请用事实说话。”
会后第三天,第一批独立观察员抵达青山村。有新华社记者、中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专家,还有一位来自深圳的网络安全工程师,名叫周野。此人三十出头,戴着黑框眼镜,寡言少语,但一进村就直奔数据中心,要求调取过去半年的所有访问日志。
赵振国亲自接待他。“你可以查任何数据,但有一个条件??查完之后,请给孩子们上一堂课,教他们怎么保护自己的信息。”
周野愣了一下,随即点头:“成交。”
接下来的日子,村庄仿佛进入了一种奇特的节奏:一边是热火朝天的冬小麦播种,一边是密集的技术审查与舆论交锋。外界关于“青山村是否过度依赖技术精英”的争论愈演愈烈,甚至有自媒体发文称赵振国为“数字封建领主”,指责他以科技之名行集权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