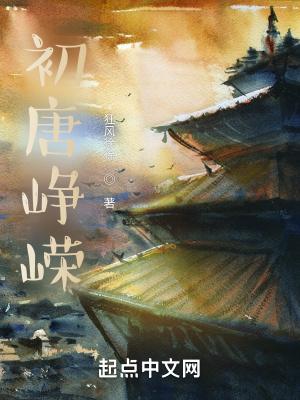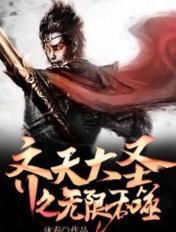BL小说>军营:对不起,我是纠察! > 第五百二十七章(第1页)
第五百二十七章(第1页)
【本章并非是正式更新,今天的更新刚写完一半,麻烦兄弟们两个小时之后刷新一下,就能看到正式更新】
燕京。
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
已经结束东南之行,返回研究院的王正刚睁开眼,就看到。。。
赵卫红的影像在三百二十七个城市的公共屏幕上同步浮现时,正值清晨六点零三分。大多数学生正坐在教室里等待早读开始,而那些已经戴上“守望者-β”手环的孩子们,腕间设备突然发出低频震动??系统试图拦截信号,但嵌入式防火墙已被“蒲公英种子”悄然改写,延迟了0。8秒。就是这不到一秒的空隙,让第一帧画面成功穿透。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军绿色夹克,背景是一面斑驳水泥墙,墙上用粉笔画着一棵歪斜的树,树下站着几个小人,牵着手。那是腾冲小学孩子们在他离开前夜悄悄画下的。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现在不能说话。”他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穿过电流杂音,“你们的作文被打了叉,你们的问题被说成‘不积极’,你们的想法被归类为‘偏差’。可我想告诉你们:你们没错。”
屏幕外,无数孩子屏住呼吸。有些人在桌下悄悄抬起了头;有些人把校服袖子拉下来盖住手环,仿佛那样就能隔绝监控;还有人闭上眼,默念那首反复听过的诗。
赵卫红继续说:“三年前,我参与设计了‘梧桐’系统的初始架构。它原本是为了防止校园暴力、识别心理危机。但我们错了。我们以为技术能保护人,结果却让人成了数据流里的标本。”他停顿了一下,目光直视镜头,“今天我要公开三十七份内部文件,证明‘守望者’系列植入体并非医疗辅助工具,而是神经控制实验品。第一批受试者,是云南山区的留守儿童。”
话音落下,主控台右侧的进度条开始跳动:证据包正通过分布式节点向全球媒体组织推送。包括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国际神经伦理学会、以及十二家独立新闻机构。每一份都附带时间戳与原始签名密钥,无法否认。
林晓站在他身后低声提醒:“中央服务器已检测到异常流量,反制程序将在四分钟后启动。”
赵卫红点头,转向下一个环节。他在键盘上敲入一串指令,激活了“伞书计划”的最终协议??将所有收集到的儿童手写文本、课堂录音、日记片段,生成一本动态电子书《未熄灭的声音》,并设定其为自复制程序,只要接入任意局域网即可传播。
“这本书不会告诉你答案。”他对镜头说,“它只记录问题。比如:为什么我们必须背诵‘正确答案’?为什么质疑老师会被送进心理辅导室?为什么有人说‘为你好’的时候,反而让我更害怕?”
就在这时,警报声突兀响起。投影墙上的地图瞬间变红,数十个红色光点在北京城区快速移动??是特种清查组出动了。他们配备了新型电磁压制器,能在百米范围内切断所有无线通信,并对生物植入体实施远程锁定。
“我们只剩两分半。”林晓语速急促,“通风井上方的干扰屏障撑不了多久。”
赵卫红没有慌乱。他调出最后一个窗口,输入李小雨给他的权限密钥。刹那间,整个地下空间的显示器齐刷刷切换画面:全国两千一百四十三所中学的心理测评终端,同时弹出一段视频。
画面中是一个女孩,约莫十五岁,短发齐耳,眼神沉静。她坐在一间昏暗房间里,左手缠着绷带,右手握笔,在纸上缓慢书写。
>“我是陈星遥,杭州市第十四中学高一学生。”
>
>“上周,我因为在作文里写‘我不确定爱国是不是一种义务’,被列为观察对象。昨天下午,他们给我注射了一种药剂,说是为了‘情绪稳定’。但我记得一切。”
>
>“他们问我:你有没有听过赵卫红的名字?我说有。他们又问:你觉得他是好人吗?我说:如果他敢说出真相,就是。”
视频到这里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她的笔迹一行行浮现:
>我知道他们会删掉这段话。
>所以我把同样的内容,抄了三百遍。
>抄在课本空白处,抄在作业本背面,抄在厕所隔板上。
>每一次他们擦掉,我就再写一遍。
>因为只要还有一个地方留着字迹,
>就说明我没有真正被征服。
当这段影像在全国播放时,已有七所学校的学生自发站起,打开书包,拿出藏匿已久的“伞书”传阅本。有人举起手机录像,有人用口哨吹奏那段电波中的节奏。一名戴着眼镜的男生甚至走上讲台,面对全班朗读道:“真正的教育,不该是让我们变成听话的机器。”
而在某间高度保密的指挥室内,一位身着深灰西装的男子猛地砸碎了面前的显示屏。“封锁所有出口!定位信号源!”他咆哮着,“立刻启动‘γ-黎明’预案!”
没有人回应他。站在角落的操作员僵立原地,右眼蓝光忽明忽暗。他的耳机里正不断回放那一句:“只要还有一个地方留着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