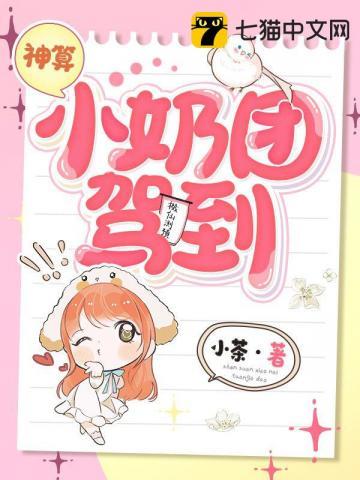BL小说>军营:对不起,我是纠察! > 第五百二十七章(第2页)
第五百二十七章(第2页)
几秒钟后,这名认知协防员缓缓摘下耳机,低声说:“我小时候……也写过类似的话。”
此时,赵卫红已完成最后一次数据上传。他拔下存储卡,用力折断,然后看向林晓:“接下来呢?”
“按原计划,分散撤离。”她递来一张地铁线路图,上面用红笔圈出一条通往郊区的废弃支线,“终点站附近有个防空洞,接应人会在那里等你。”
他摇头:“我不走。”
“你说什么?”林晓愣住。
“李小雨回来了,那就说明还有更重要的事没完成。”他盯着仍在闪烁的监控画面,“她不是为了救我才现身。她是来传递信息的??‘启明波段’已经开始共振了。”
正如他所说,此刻在全国各地,一些原本处于潜伏状态的“蒲公英种子”程序突然自行激活。它们并不攻击系统,而是引导使用者进行特定思维训练:逻辑推演、隐喻理解、矛盾辨识。这些练习看似普通,实则是针对“守望者”神经反馈机制的逆向刺激。
成都一名十二岁的男孩在做完一道数学题后,忽然发现自己的手环闪烁出陌生代码。他凭着记忆将其转译,竟是一句话:“你比系统更快。”
西安某重点中学的心理协管员在例行巡检时,发现自己无法对一名学生的测谎反应做出判断。因为那个女生盯着她的眼睛说:“你在怕我,对吗?”
最令人震惊的是,在第七研究院内部,一台用于监测“守望者-β”运行状态的核心主机,突然输出了一段异常日志:
>【警告】检测到大规模意识协同现象
>初步分析:个体怀疑意识正在形成集体神经共鸣
>命名建议:代号“萤火”
赵卫红看着这些实时反馈数据,嘴角微微扬起。他知道,这场战争的本质早已改变??不再是人对抗机器,而是思想唤醒思想。
“我要回去。”他说。
“回哪儿?”林晓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家。”他站起身,披上外套,“他们一定会去那儿蹲守。但也是唯一可能再收到她消息的地方。”
林晓沉默片刻,最终点头:“我陪你。”
两人从另一条隧道撤离,避开主干道,穿行于城市地下管网之间。途中经过一段坍塌区域,只能匍匐爬行。泥水浸透衣裤,空气中弥漫着铁锈与霉味。就在即将抵达出口时,前方忽然传来微弱的哼唱声。
他们停下脚步。
那是一首童谣,音色稚嫩,带着颤抖:
>“小伞花,开呀开,
>雨来了,也不怕。
>妈妈说,心里面有光的人,
>走夜路也不会摔跤。”
赵卫红轻轻拨开挡路的钢筋网,看见一个小女孩蜷缩在管道尽头,怀里抱着一只破旧布偶。她约莫七八岁,校服上别着心理协管员见习徽章,可左臂上的“守望者”贴片已被撕去,伤口结了痂。
“你是谁?”他轻声问。
女孩抬头,眼里含泪:“我叫田苗。我在等……等一个拿黑伞的人。”
赵卫红心头一震。他掏出钥匙扣,举到她面前。
女孩怔了几秒,随即伸手从布偶肚子里掏出一张折叠整齐的纸条,递给他:“她说你会来。还说如果你带来了光,就把这个交给你。”
纸条展开,只有短短一行字:
>“明晚八点,重启‘飞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