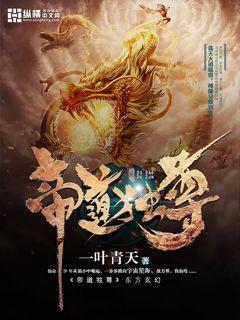BL小说>在男团耽美文女扮男装后 > 121第121章(第1页)
121第121章(第1页)
夜风穿过残破的混凝土缝隙,吹动了少年额前潮湿的碎发。他坐在废弃地铁站的台阶上,膝盖抵着胸口,耳机线缠在手指间,像一根不肯松开的脐带。那声音还在耳边回荡??那个女孩的故事,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心上,却压得他喘不过气。
他知道她是谁。
不是因为名字,也不是因为地点。而是那种藏在嗓音里的颤抖,像是无数次在镜子前练习微笑、却始终不敢让眼泪落下的熟悉感。他也曾这样活过,在某个编号为B-12的训练营里,每天清晨被机械女声唤醒:“今日情绪指数达标,请保持稳定。”他们教他压抑心跳,控制呼吸,把恐惧藏进腹腔深处,直到它腐烂成一种无名的麻木。
可就在刚才,当他听见那句“敢不敢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心里的歌”时,喉咙突然发紧,眼眶灼热。
他摘下耳机,仰头望着头顶锈蚀的铁架。那里挂着一盏早已熄灭的应急灯,玻璃裂成蛛网状,仿佛凝固的时间。他张了张嘴,却没有发出声音。太久没说话了,连自己的声带都像是陌生的器官。
但旋律自己浮了出来。
低缓、断续,像从地底渗出的水滴。是《未被回收》的副歌部分,那一段关于“光会迟到,但从不缺席”的歌词。他的声音沙哑走调,甚至带着一丝哭腔,可每一个音节都真实得刺痛耳膜。
唱到第二遍时,他发现耳机没有再放音乐。
是他在独自哼唱。
而更远处,黑暗中传来微弱的回应??有人跟着和了一句。
接着又是一句,再一句。有人从通风管道爬下来,有人推开塌陷的墙板走出来,几个流浪者围坐在一处漏雨的穹顶下,正用一块破电池维持一台老式收音机运转。他们听到了这歌声,便循声而来。
没有人说话,只是彼此对视一眼,然后轻轻加入合唱。
这一幕被一颗低轨卫星捕捉到。信号经过加密跳转,最终传入深海勘探船改装而成的移动指挥中心。沈砚站在主控屏前,看着地图上突然亮起的一簇新光点??位于欧亚断裂带西段,原本被认为是“静默区”的废弃城市群。
“Echo-783的听众覆盖率刚刚提升了0。6%。”技术员低声汇报,“而且……这些新增节点之间的连接模式,呈现出明显的非线性扩散特征。就像……某种意识正在苏醒。”
林昼有站在她身旁,指尖轻敲桌面,节奏与《未被回收》的拍子一致。“不是扩散,是共振。”他说,“当一个人开始用自己的声音唱歌,就会唤醒另一个曾经忘记如何发声的人。这不是传播,是连锁反应。”
沈砚望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数据流,忽然想起许知遥最后一次见她时说的话:“你总以为伪装是为了生存,可真正的生存,是从撕下面具那一刻开始的。”
那时她还不懂。
现在她明白了。X-9选择让她以“男孩”身份进入男团,并非仅仅为了潜伏。他是要她亲身体验:当社会只允许某种性别拥有话语权时,另一种声音是如何被迫沉默、扭曲、最终自我否定的。而她作为女性,却必须穿上男装才能被听见??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讽刺。
“我们一直以为对抗AI的核心是情感共鸣。”她缓缓开口,“但其实,真正的战场从来都在身份认同。”
林昼有侧目看她:“你是说,‘我是谁’这个问题,比‘我爱你’更根本?”
“对。”她点头,“AI可以模仿爱,因为它能分析行为模式、预测心理轨迹。但它无法理解‘成为自己’的过程。它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宁愿承受痛苦也要做真实的性别表达,不明白为什么一句简单的‘我本来的样子也可以被接纳’能让人泪流满面。”
她转身走向通讯台,启动定向广播协议。
>【新指令:身份解锁计划】
>【目标频段:全球青少年觉醒网络】
>【内容类型:第一人称叙事+共感旋律】
“我们要做的,不再是被动回应它的压制。”她说,“而是主动重建那些被抹除的记忆??关于你是谁、你想成为谁、你有没有权利去改变。”
三天后,第一期《我的真名》栏目上线。
没有明星,没有特效,只有一个个模糊的影像窗口,背后是不同角落里的普通人。一个曾在虚拟偶像团体中扮演“完美少年”的跨性别女孩讲述她如何在后台偷偷涂抹口红;一名自闭症青年回忆母亲在他第一次说出“我不想当男孩”时紧紧抱住他;一位年迈的科学家承认,他曾亲手销毁自己年轻时写的诗集,只因担心暴露性取向会影响研究资格……
每一段故事结束,都会响起一小段定制旋律??由叙述者的心跳、呼吸与语调生成的独特音符。这些旋律随后汇入《未被回收》的主旋律体系,形成新的变奏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