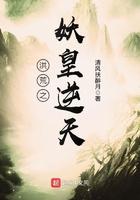BL小说>我才是徒弟们的随身老爷爷? > 第三章 代码无敌(第3页)
第三章 代码无敌(第3页)
阿木浑身一震。
他终于明白,林小满为何临终不留一字。因为答案不在言语里,而在行动中。这位老人一生未曾自称“高人”,却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世人:所谓修行,不过是坚持做一个不肯遗忘的好人。
三日后,阿木宣布:守忆寺不再设围墙,不再藏秘典,所有石板拓印分发各地,所有善录公开誊抄,任何人皆可前来学习《护心曲》,带走一份《续光谱》。
“我们要让记忆,回到它本该属于的地方??民间。”
消息传出,四方涌动。有人跋涉千里而来,只为亲手刻一块石板;有盲童在父母带领下,摸着盲文石板流泪背诵;更有曾参与焚书的前官吏,跪在庙前忏悔,请求加入誊录队伍。
而那支曾撤退的三千铁甲,半年后再次抵达山脚。但这一次,他们卸甲弃戈,每人背负一块石料,为首将军亲自扛着一块刻有“悔”字的青碑。
“我已辞官。”他对阿木说,“从今往后,我愿做个守碑人。”
阿木点头,带他走向庙后山坡。那里,新立了一片碑林,每一块都属于无名者。将军放下石碑,拿起刻刀,颤抖着手,一笔一划写下:
“丁酉年八月,边军士卒张六斤,私藏难民婴儿于粮袋中,冒死送出关外。后遭鞭刑三十,流放北荒,不知所终。”
刻毕,他重重叩首。
风起,林梢簌簌作响。
do……re……mi……sol……la……si……do……
琴音再起,不知来自何方,却分明处处皆闻。
多年后,一位考古学者重返北岭,在庙宇遗址发掘出大量陶片、碎瓦、旧书残页。当他试图用仪器分析时,惊人发现:所有文物的分子结构中,竟嵌套着同一段音频频率??正是《护心曲》的基音。
更诡异的是,每当月圆之夜,这些碎片会自发共振,发出微弱和声,持续整整七十二秒。
学者百思不得其解,直至某夜,他梦见一位白发老者坐在星空下,怀抱骨琴,微笑道:
“你以为你在研究历史?
其实,是历史在呼唤你。”
梦醒,他翻开笔记,发现自己无意识写下一句话:
“我愿成为下一个记得的人。”
翌日,他放弃京城职位,留在北岭,建起第一座“平民记忆馆”。
而此时,在遥远的西域沙漠,一支商队夜宿绿洲。篝火旁,孩童问父亲:“什么叫‘善’?”
父亲沉默良久,从行囊中取出一本破旧小册,翻开一页,轻声念道:
“庚戌年六月初九,晨雾未散,有童子跪于断梁之下,以口含清水,滴入昏迷妇人唇间三十六次,终使其苏醒。问其名,答曰:‘我叫小满。’”
孩子睁大眼睛:“后来呢?”
父亲望向星空,微笑:“后来啊……很多人都成了‘小满’。”
风过沙丘,卷起一粒晶莹??那是埋藏千年的陶片,在月光下闪烁如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