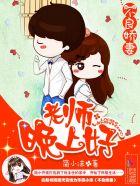BL小说>文豪1879:独行法兰西 > 第355章 我要送你一间剧院(第1页)
第355章 我要送你一间剧院(第1页)
阿尔芒?标致紧紧握住德拉鲁瓦克的手,语气急切:“德拉鲁瓦克先生!这太疯狂了!订单,超过三千辆!
上帝,三千辆!我们之前的协议必须修改了!我们应该立刻成立‘索雷尔-标致机械制造公司’!
我可。。。
那年冬天,我最后一次见到祖父,是在广州老宅的天井里。他蹲在地上,用炭笔画着一座桥??不是石桥,也不是木桥,而是一座悬在空中的桥,两端都没有落脚点,桥下是深不见底的雾。我那时才八岁,踮着脚看他画,问他:“爷爷,这桥通到哪儿去?”他头也不抬,只说:“通到记不得的地方。”
多年后,当我站在索邦大学讲堂前,面对近百双眼睛,我才明白那座桥的意义。它不通向任何地理上的彼岸,而是通往记忆本身??那些被时间掩埋、被语言遗弃、被身份割裂的片段。我们每个人都在走这样一座桥,脚下是虚无,头顶是星辰,手中握着的,不过是一张写满遗忘的路线图。
讲座结束时,掌声比预想中热烈。一位戴眼镜的女生举手提问:“林先生,您现在被视为‘跨文化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您是否担心,这种标签反而会限制您的创作自由?”
林昭站在讲台边,手指轻轻摩挲着笔记本边缘。窗外雨丝斜织,打在玻璃上发出细碎声响。他沉默了几秒,才开口:“三年前,如果有人叫我‘跨文化作家’,我会激动得整夜睡不着。但现在……我不确定这是赞美还是囚笼。”台下安静下来。
“我曾以为,我的价值在于‘不同’??一个中国人写法国故事,或一个东方人解构西方孤独。可后来我发现,真正的共鸣,从来不是来自异域风情的猎奇,而是来自人类共通的情感结构。比如失去,比如误解,比如爱一个人却无法表达。”他顿了顿,“所以,我不拒绝这个标签,但我也不属于它。我只是个试图诚实写作的人。”
问答环节结束后,伊莎贝尔在走廊等他。她撑着一把墨绿色的伞,发梢微湿。
“讲得很好。”她说,“尤其是最后一句??‘我只是个试图诚实写作的人’。这句话会被引用很多次。”
林昭苦笑:“希望不是被断章取义。”
两人并肩走入雨中,沿着塞纳河缓步前行。河水灰绿,载着落叶与倒影缓缓东去。伊莎贝尔忽然问:“你有没有想过回国?”
林昭一怔。
“不是指定居,”她补充道,“而是回去看看。你的小说里总提到广州、香山、珠江口的老屋,可这些场景全都像是从记忆深处打捞出来的碎片,带着水汽和模糊的轮廓。你不怕它们再过几年,就彻底沉没了么?”
林昭望着河面,没有立刻回答。他知道她说得对。这些年,他在巴黎写中国,笔下的一切都经过双重过滤:一是时间和距离的晕染,二是法语思维对汉语意象的重塑。他写的“故乡”,早已不是地理意义上的那个南方小城,而是一个由乡愁构筑的心理空间。
“我怕。”他终于说,“我怕回去之后,发现一切都变了;更怕什么都没变,变的是我自己。”
伊莎贝尔侧头看他:“那你宁愿让它停留在文字里?”
“也许吧。”他轻声说,“至少在那里,我可以决定哪扇门开着,哪棵树还在开花。”
他们走到艺术桥附近时,雨停了。桥上挂满了旧锁,锈迹斑斑,像一段段凝固的爱情誓言。林昭想起自己曾在一篇散文里写道:“巴黎人把爱锁在铁链上,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心能长久;而中国人把思念藏在信里,是因为他们害怕言语一旦出口,就成了诀别。”
“下周,《新法兰西评论》要为《回声街》办一场专题讨论会。”伊莎贝尔转移了话题,“主编想请你谈谈‘语言与失语’的主题。你会去吗?”
“当然。”林昭点头,“那是我近年最贴近心脏的作品。”
伊莎贝尔笑了:“你知道吗?有位心理学教授读完说,这篇小说让他想起了‘代际创伤’的概念??有些痛苦无法言说,只能通过仪式传递。那位老妇每天朗读空白信件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哀悼练习。”
林昭若有所思:“我写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些理论。我只是记得我妈也曾这样。我爸去世那年,她每天晚上都会对着他的枕头说话,仿佛他还躺在旁边听着。我说‘爸已经走了’,她看着我,说:‘我知道。可如果不说了,他就真的不在了。’”
伊莎贝尔轻轻握住他的手腕:“所以你写这个故事,其实是在替母亲发声?”
林昭闭上眼,点了点头。
那一刻,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所有的写作,或许都不过是在完成一场漫长的对话??与逝者,与童年,与那个曾经以为必须选择“东方”或“西方”的年轻旅人。
几天后,讨论会在一家小型剧场举行。到场的观众不多,但几乎全是文学圈的核心人物:诗人克莱尔?莫雷诺、批评家菲利普?杜兰、刚获龚古尔奖提名的小说家玛德琳?罗什。主持人开门见山地问道:“林昭先生,《回声街》中的‘空白信纸’象征什么?”
林昭坐在聚光灯下,声音平稳:“它可以是许多东西??失语、遗忘、未竟之言、压抑的情感。但对我而言,它首先是‘爱的证据’。即使内容为空,书写行为本身已构成一种存在。就像我们写下日记,明知无人阅读;就像父母对孩子说‘我爱你’,哪怕孩子已熟睡。”
台下有人低声啜泣。
另一位学者追问:“您认为非母语写作会影响情感的真实性吗?毕竟,您用法语构思,再译成中文发表。”
这个问题像一根针,刺入他最敏感的神经。
“影响当然存在。”林昭坦然道,“法语教会我精确与克制,汉语则唤醒我的直觉与诗意。我在两种语言之间来回穿梭,就像在两座岛屿间架桥。有时桥塌了,词不达意;但也有时候,正是这种断裂,让我看见新的可能。”
他举了个例子:“中文里‘想念’是一个词,而法语要用‘manquerdequelqu’un’(某人缺失于我)来表达。前者是状态,后者是动态的空洞。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才真正理解了思念的本质??它不是温柔的回忆,而是持续的缺席之痛。”
全场静默数秒,随后爆发出掌声。
散场后,亨利?克莱蒙走上前来,拍了拍他的肩:“你变了。”
“怎么讲?”
“以前你总想证明自己够‘法国’,或者够‘中国’。现在……你只是林昭。”
林昭笑了笑,没说话。他知道,这句评价,胜过千篇赞誉。